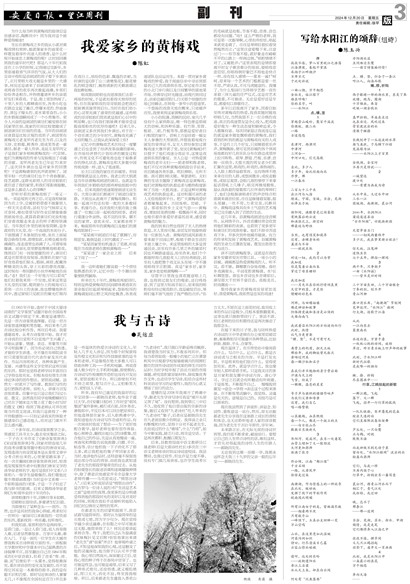自1993年开始,选材于中国大量诗词曲的“文学鉴赏”试题开始在全国高考语文试题中固定下来,难度是递增的。先是一首古诗鉴赏选择题,后是一首古诗鉴赏选择题和笔答题,再后来考几首古诗比较分析作答,再往后考词。我要感谢高考,从考古诗鉴赏开始,我才对古诗真的自觉和不自觉地产生兴趣了,开始从意象、情感、表达、形象等方面学习和揣摩了。因为你必须自己悟透,才能给学生讲透。全不像在阜师院读书时只需要知道历代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作品内容和形式、各种体裁产生、发展、兴盛等这些文学史常识这些空洞的东西。那时也觉得老师学问丰富而自己学得也很充实,但根本没有萌生古体诗近体诗的创作想法,更别说词赋。虽然大一时就开了写作课,教我们写作的是位姓陈的老师,宿松人,讲课方言发音很浓重,印象中也只是让我们写过小说、散文。虽然我在同学夜晚酣睡时自己伏在下铺床边方凳上花了数小时写好的散文《蝉》得到了陈老师认可并在班级当作范文宣读,但我只是获得了一种开窍般感悟——只有记录真实的体验才能感染自己感动他人,而对这门课并不怎么感兴趣。
二十多年前,在诗词鉴赏教学之余,常感觉工具书太少,趁去安庆集训之际,一下子在大书市买了《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回家对照连续几年的高考诗歌鉴赏题中相应的唐诗宋词,发现选项内容设置基本是从鉴赏文章中分考点析出来的,心里便觉踏实多了。有一次在翻阅《唐诗鉴赏辞典》时,惊喜地发现鉴赏作者中有教我们唐宋文学的汤华泉老师名字,他可是我们中文系八0级和八一级学生最敬佩的,我们敬他比敬牛维鼎副教授(当时是中文系唯一一个职称最高的)更多,于是一下子拉近了我与辞书的距离。后来又偶得汤华泉老师《为80级毕业四十年而作》:
讲席相逢四十年,回眸往事未如烟。
切磋相长留佳话,多谢诸生忆旧篇。
当即便有了某种念头——创作。当然,也许是其时的我身心俱疲,希求有另一世界另一家园可以承载我的一切负面的东西,重新找到一些乐趣,有所寄托。
但我知道,鉴赏和创作是两码事,一是看门道,一是让人看门道,说人容易做人难,后者显然难很多。万事开头难,难在入门。于是一面托一位学生在大城市替我购买古诗押韵方面的书,一面根据大学教材和中学课本中自己最熟悉的古诗揣摩平仄,甚至翻出自己在1984年购买的《中原音韵》,但看了音系“帮、滂、端、泥”后便似乎一头雾水,觉得很难深究,重在讲语音的变化及发展的,而不觉得它其实是一本难得的韵书,真的是有眼不识和氏璧。那时写近体诗的人寥寥无几,(不像现在全国有近百万)并且多是一些退休的热爱古诗词的文化人,年轻人几乎无人涉足,因为那个时候获得及传授文化知识和写作技能依靠的是书本和老师,不是像现在绝大多数人可以借助各种工具——手机和电脑。再说普通人极少有什么手机和电脑,即使拥有,古诗词写作检测软件恐怕也没有开发出来,更别说相关平台。所以即使有不吐不快之欲望,想写点什么,又怕贻笑大方,更怕误人子弟。
所幸,我有早已遇见的我最好的忘年交同事——郝晓昌老师,他毕业于震旦大学,在《安徽日报》社工作时受“胡风集团”案件影响,被打成右派,回乡务农,兼做郎中,平反后本可以回合肥原单位,但他选择留在家乡,后入职鸦滩中学。我知道他有古诗词写作功底和作品,有一次闲谈时我说了想法——为了更好地配合教学,最好老师也要有创作体验。他心领神会,翻找出他自己的诗歌集,结合他自己的作品,先是认真地慢读一遍,再春风和煦般告诉我韵脚、白脚、平仄、粘连等,估计他怕我一下子消化不了那么多,就让我把他的集子带回家去看。当时,他讲他作品时,还特意毫不保留地说出部分作品的背景,由此我也就知道了老先生的那段罗曼蒂克的过去。从他的轻缓悠长的叙述语调和迷离朦胧神情中,除了潜意识地感觉并非全是像大学老师传播——马克思说过,“愤怒出诗人”。(后来又听说原话是“愤怒出诗作”,是古罗马一位诗人说的)但“生活是艺术之源”是绝对的真理,我更多的是分明感受得到他的那段时光的美好以及对美好的回味,到现在我似乎还能听到他陷入回忆时忘情而又理性的笑声。
在郝老先生的启蒙和鼓励下,我尝试着写最简单的。那时认为最简单的是五绝或七绝,因为字少句少。现在觉得字越少表达越难,在有限之中尽可能表达无限,能简单得了么?何况还要讲起承转合等。终于,我把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咏梅》(见文后附)怯怯地拿出来请“老先生”请“前辈”斧正!他审视吟诵之后,不知是他深知我的心境,还是触及了他的灵魂深处,他当即予以认可并予勖勉。我心里自然高兴,深深谢过之后,觉得心里的种子终于在春风中冒芽了。也可能是性急,也可能是渴望,后来又写了几种形式绝句,还没悟透,就又模拟填词,胃口太大,消化不良,终至畏畏缩缩。所以,后来郝老先生邀我入香茗山“九老诗社”,我只能以年龄悬殊而婉辞,我清楚我当时实力,不敢忝列其中。但每当看到如我一般瘦小的他伫立在萧瑟秋风中注视着学校报墙玻璃内的用图钉摁住的宣传诗词创作成果的师生共同作品时(当时学校申报了语法方面的市级课题,研究需积累原始材料,除收集优秀作文外,也动员学生写诗,拟结合这些材料谈语法学习的必要性),我的内心就又增添了前行的动力。
遗憾的是2008年我离开了鸦滩中学,跟老先生学诗写诗可真是“刚开头却又煞了尾”。没有想到,我到望江三中后不久,竟收到了他自资出版的全新的诗集,随后又收到“九老诗社”托人带来的“九老诗社”集子,后者应是郝晓昌先生在九老面前推介的明证。我拜读之余只有惭愧和内疚,觉得十分对不起老先生,先前说过的什么“赓续”,什么“乃绍”,如今中断实践,缺乏行动,则全是空话。于是再次蓄积、酝酿以期发力。
后来,县教育局高中语文教研员江晟老师(后是大雷诗社社长)多次在三中语文老师座谈时倡议诗词进校园。我虽赞同,也做过宣传,但也许是力度不够,没有专门搞几场讲座,也许学生高考压力太大,不愿在这上面花时间,故而收上来的作品自是极少,且根本要推翻重来,这事也就只能指望同行了。事虽不谐,但江老师的信任和期待还是再次催动了我那念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与同样热爱古诗词的王中华老师在办公室里切磋切磨,渐渐熟知尽可能避开各种禁忌,比如挤韵、撞韵、平头、合掌等。
现在退休了,在引带幼孙中偷闲看点什么,写点什么,记点什么,都是古诗词或与之相关的内容。半是打发光阴,半是将来给他们留点什么,觉得更加充实。此外,就是学点什么,我也像年轻人那样看看手机,只是我关注的多是方家和朋友圈中诗词内容,虚心学习,学过之后就会有所触动有所刺激,于是练笔,不断提升自己。 慢慢按照激发→意念→孕育→表达这个过程来准备,在不断练笔活脑中,我觉得,灵魂是先天的,意境是自己的,而技巧是可以师承的。
现在我虽然到了讲波折、讲悬念、知词性、重炼意这一站台,然而,却无法跟郝老先生分享我在这条路上成长的喜悦和体会,也无法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因为老先生于2021年辞世,享年96。
未来路正长,在无际无涯的诗词世界里,我仍需不断求索,破浪前行。要想让自己的人生带点诗性的话,唯有这样,才首先对得起我的诗性人生的引路人——郝晓昌先生。
无论我到达哪一站哪一亭,我都永远怀念大我三十九岁的父亲一般的忘年交——郝晓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