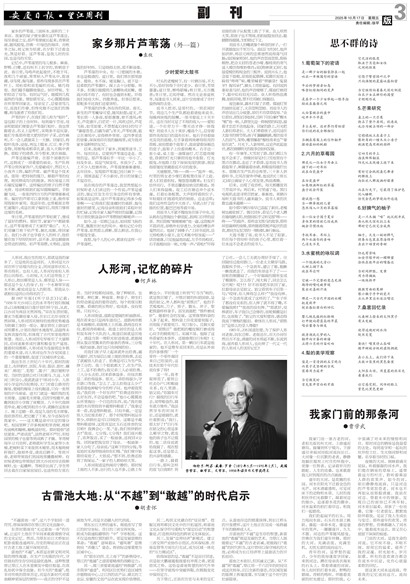家乡的芦苇荡,三面环水,面积约二十来亩。我家的屋子便坐落在这芦苇荡边,每至春夏之交,那芦苇便疯长起来,青翠欲滴,随风摇曳,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而秋冬之际,则又转为枯黄,在夕阳下泛着金光,煞是好看。这芦苇荡,是我儿时的乐园,也是鸟的天堂。
记忆中,芦苇荡里的鸟儿极多。麻雀、野鸭、白鹭,还有叫不上名字的,皆栖息于此。春日里,鸟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和几个顽童,常常钻入芦苇丛中,捉迷藏,寻鸟窝,掏鸟蛋。那些鸟窝多筑在芦苇杆上,用枯草和羽毛编织而成,精巧得很。我们蹑手蹑脚地靠近,屏住呼吸,生怕惊动了母鸟。有时运气好,能摸到几枚温热的鸟蛋,便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带回家去。母亲见了,总要责骂几句,说我们作孽,但终究拗不过我们的馋嘴,将鸟蛋煮了给我们吃。
芦苇的叶子,在我们那儿称为“粽叶”,是包粽子的上佳材料。每到端午节前,母亲和姐姐们便要去芦苇荡打粽叶。我也常跟着去,名义上是帮忙,实则多半是玩耍。她们专拣那些宽大肥厚的叶子采,动作麻利,不一会儿就能采上一大捆。回家后,将粽叶洗净,浸泡,再包上糯米、红豆、枣子等食物,用细绳或稻草扎紧,放入大锅中煮熟。那粽子的清香,至今想来,犹在鼻端。
芦苇还能编芦席。在那个困难的年代,这倒成了一项重要的副业。生产队将芦苇分到各家各户,先要破成片,然后大人小孩齐上阵,编织芦席。破芦苇是个技术活,需用一把特制的篾刀,顺着芦苇的纹理,将其劈成均匀的细条,再在场基上用石磙反复碾平,这样编出的席子自然平整光滑。母亲和姐姐们起早摸晚编织,手指翻飞间,一张张四四方方的芦席便渐渐成形。编好的芦席可以拿到街上卖,换些零用钱贴补家用。我虽年幼,也常被派去帮忙递篾片,或是在席子编好后,用剪刀修剪边缘的毛刺。
冬日里,芦苇荡里的芦苇枯黄了,便成了最好的燃料。那时节,家家户户都缺柴火,这芦苇荡便成了大家的“柴山”。大人们用镰刀割下枯芦苇,捆扎成捆,背回家去。我们小孩子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捡拾铺在地下厚厚的枯叶,虽不多,却也颇能体会劳动的喜悦。枯芦苇易燃,火势旺,是烧饭的好材料。只是烧得太快,需不断添柴。
芦苇荡的中央,有一口宽阔的水塘,水也是极清的。夏日里,我们常在那里游泳、摸鱼。水不深,刚及胸口,底下是一层柔软的芦苇落叶,踩上去十分舒服。鱼不多,但偶尔能摸到几条鲫鱼或泥鳅,便高兴得不得了。有时也会遇到水蛇,吓得我们哇哇大叫,四散奔逃,但事后想来,那蛇多半比我们还要害怕。
芦苇荡的四季,各有各的风景。春天,新生的芦苇嫩绿可爱,随风轻摆;夏天,芦苇长到一人多高,郁郁葱葱,密不透风;秋天,芦花盛开,白茫茫一片,风吹过时,芦花飞扬,如雪如絮,不禁想起《诗经》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冬天,芦苇枯黄,挺立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坚韧。这四季更迭的景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对家乡最鲜明的记忆。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到城里读书、工作。每次回去,总要到芦苇荡边走走。奇怪的是,那芦苇荡似乎一年比一年小了。问及乡亲,说是气候变化,水流少了,加上不少人挖塘养鱼,芦苇荡便渐渐萎缩。去年回乡,发现那芦苇荡已经只剩下一小片,周围盖起了不少新房,昔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
站在残存的芦苇荡边,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过的一个传说:芦苇是通灵的,能记住发生在它身边的所有事情。如果真是这样,这片芦苇荡该记得多少故事啊——记得我们捉迷藏时的雀跃、掏鸟蛋时的嬉笑,记得母亲和姐姐们采粽叶时的忙碌,记得全家人编芦席时的温馨,记得冬日里炊烟袅袅中芦苇燃烧的噼啪声……
如今,这一切都已远去,如同那飞扬的芦花,飘散在时光的风中。唯有记忆中的芦苇荡,依然那么清晰,那么鲜活,在我心中摇曳生姿。
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该有这样一片芦苇荡吧。
少时爱听大鼓书
村头的老槐树下,有一片晒谷场,不大不小,恰好容得下全村老少。春日里,芳草萋萋;夏日里,蝉鸣聒噪;秋日里,五谷飘香;冬日里,北风呼啸。然而无论春夏秋冬,每逢说书人到来,这片空地便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去处。
说书人姓刘,是邻村的,一到农闲时节,周边几个生产队都抢着请他来说书。每晚两块钱的报酬,一部书要说上十天半月,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收入——要知道,一个壮劳力干一整天活才挣一块钱呢!刘说书人五十来岁,瘦高个儿,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他右手持着油光发亮的鼓槌,左手拿着两块磨得锃亮的简板,面前摆着个鼓架子,鼓面蒙着深褐色的皮子,鼓架子上挂着块醒木。右手边一张小桌,桌上放一盏煤油灯,灯芯捻得极低,昏黄的灯光只够照亮他半张脸。灯光摇曳,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倒显得那皱纹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
天刚擦黑,“咚——咚——”鼓声一响,村里的男女老少便扛着板凳往场子上赶。老人们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踱来;妇女们结伴而行,手里还攥着没纳完的鞋底;男人们来得最晚,收工后在塘边冲个凉水澡,扛着长条板凳,大声招呼着找位子。年轻媳妇们抱着吃奶的娃娃,边走边哄;我们这些性急的半大孩子,早就占好了前排的位置,眼巴巴地等着开场。
刘说书人不紧不慢地坐在场子中央,先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搪瓷缸,抿两口自带的凉茶。然后简板“啪啪啪啪”地一敲,这简板声不算洪亮,却格外有穿透力,全场的嘈杂声戛然而止。他润了润嗓子:“上回书说到,岳元帅枪挑小梁王,金兀术帐中惊坐起……”话音刚落,只见他猛地站起,左手作持枪状,右手鼓槌向前一刺,大喝一声:“看枪!”吓得前排的孩子从板凳上跌了下来。众人哄然大笑,那孩子也不哭闹,拍拍屁股坐回去,眼睛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下文。
刘说书人的嘴就像个神奇的匣子,一打开就能放出千军万马。说《岳飞传》时,他声如洪钟,将岳元帅的忠勇凛然说得荡气回肠;说《杨家将》时,他的声音忽高忽低,抑扬顿挫,把佘太君的苍老沙哑、穆桂英的英气逼人模仿得惟妙惟肖;说《隋唐演义》时,他最爱模仿程咬金的三板斧。说到兴头上,他会放下鼓槌,原地抡起胳膊,双脚在泥地上跺得“咚咚”响,嘴里喊着“劈脑袋!鬼剔牙!掏耳朵!”,额头上青筋暴起。有回说到秦琼卖马时,他的声音哽咽了,煤油灯映照下,眼中似有泪光闪动。众人听得热血沸腾,如临其境,禁不住用袖口抹眼泪。
夜色渐深,露水打湿了衣襟。煤油灯里的油快见底了,火苗忽明忽暗。刘说书人的声音显出几分疲惫,却仍不肯草草收场。“众位看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醒木“啪”地一响,人群里先是一阵惋惜的叹息,接着才恋恋不舍地起身。回家的路上,月光把人影拉得老长。大人们牵着孩子,还沉浸在大鼓书的情节里;孩子们蹦蹦跳跳,模仿说书人的语气、架势,嘴里嚷着“穆桂英来也”“秦琼在此”。月光下,人影绰绰,议论声此起彼伏,都在猜测明天的故事会如何发展。
有一年寒冬,大雪封了路,我们都以为他不会来了。傍晚时却见村口雪地里有个黑点在挪动,走近了才看清,是刘说书人背着鼓架子,裤脚裹着冰碴,棉鞋湿得能拧出水。那晚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三十多人挤着听书,北风在窗外呼啸,他说的《三侠五义》却让满屋子人心里发烫,热血沸腾。
后来,出现了收音机,每天都播放刘兰芳说评书;再后来,村里通了电,黑白电视机走进寻常百姓家。渐渐地,来晒谷场听大鼓书的人越来越少,说书人来的次数也越来越稀……
如今那片晒谷场早已盖起了新房,老槐树也被砍掉了。偶尔回乡,看见几个老人蹲在墙角晒太阳,恍惚间似乎又听见那“咚——咚——”的鼓声。那些金戈铁马的故事,那些屏息凝神的夜晚,那些随着简板声起伏的悲欢,都化作记忆里的一缕轻烟,渐行渐远。
大鼓书散了场,说书人不见了踪影。但在每个曾经听书的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位永远不会老去的说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