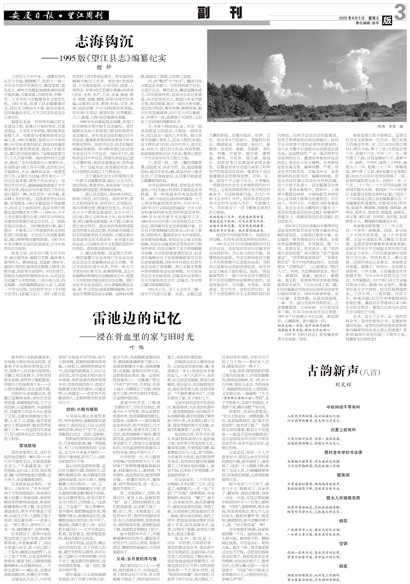窗外的日光斜斜落进来,在地板上洇出块淡金的斑。老婆孩子在出租房里该是正忙的,我独个儿在自家空屋里转,书翻了两页就搁下,手机划得指尖发僵,索性拎了拖把拖地,给窗台上的绿萝浇了水 —— 可心里空落落的,怎么也填不满。
年轻时从老家蹚出来,转眼已是鬓角染霜,却仍在生活里晃荡。新疆到皖西南,几千公里的路,山是叠着的,水是绕着的,回趟望江的念头在心里盘了又盘,总被杂事撞得七零八落。人老了,心就脆,刚才望着窗台上那盆绿萝,眼泪忽然就涌了上来 —— 许是该写写老家了,写写那些在记忆里发着光的人和事。
雷池故地
我的老家望江县,是钉在皖西南边缘的一颗小星 —— 长江中下游的北岸,古雷池就卧在这儿,“不敢越雷池一步” 的典故,是打这儿生的。每次想起,胸口总悄悄胀起点骄傲:这方水土,原是藏着故事的。
它本就该是灵秀的。一面靠山,三面环水,“水乡泽国” 四个字担得稳稳的。春末看田埂上的紫云英漫成海,夏初听稻浪里的蛙鸣滚成团,秋深时稻穗垂得压弯了腰,冬天的雪落进麦田,软乎乎的像盖了层棉。从前日子苦,人靠稻子麦子活命,却总被水欺 —— 老辈人念 “望江望江,面对长江,大水一来,淹得精光”,念得牙酸。
后来就好了。改革开放的风也吹进了这方水泽,政府领着修堤,水患渐渐歇了。2022 年带妻儿回去,距上回已隔了二十多年,脚刚沾地就愣了:长江上架了大桥,白花花的桥身跨着水,像道飞虹;马路宽得能跑两辆车,从县城到安庆,一个钟头就到 —— 搁从前,是要坐着船或拖拉机,折腾大半天呢。
县城也认不出了。小时候觉得 “大得走不完” 的街,如今立着高楼,商铺的招牌亮得晃眼,人挤着人,闹哄哄的都是生气。连回家的路都迷了:后山父亲的坟,若不是姐夫和内弟开车领着,我怕是要在树林里绕半天。生我养我的地方,竟成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模样。可越这样,心里越念 —— 念那些不在眼前的人,念那些埋在时光里的日子。
奶奶:小脚与暖阳
父亲是从潜山县逃荒来的。爷爷走得早,刚解放那年就病没了,我没见过,只从父亲零碎的话里,拼出个 “苦” 字。记忆里跟我们过过一段的,是奶奶。
奶奶家的茅草房在我家屋后,几步路的距离,喊一声就能应。木门上有块焦黑的印,父亲说,是当年日本鬼子烧的 —— 那印子像块疤,趴在门上,也趴在奶奶的日子里。
最记挂的是奶奶的脚。是旧社会裹的小脚,我那时小,总蹲在她脚边看。她洗脚要先烧盆热水晾着,坐在小凳上,慢慢解脚上的白粗布。一层,又一层,布上的白屑簌簌往下掉,里头裹着的哪是脚?蜷成个肉球,趾头往脚背里勾,皮肉泛着不见天日的白,白得瘆人。“这就是三寸金莲?” 我心里嘀咕,却不敢问。她把脚泡进水里,慢慢掰开趾头,趾缝里是红的,像藏着没流出来的血。洗干净了,擦层粉,等脚干透了,再一层层把布裹回去 —— 大半天就这么耗着,我看着急,她却慢悠悠的,像是在跟什么较劲。
后来才知道,这是苦。缠足是旧时候的恶,为了合男人的眼,硬生生把骨头拗弯。孙中山废了这陋习,可奶奶的脚,早回不去了。她走路总拄着拐杖,没拐杖就扶着墙,一摇一晃的,像风中的芦苇。
那年盛夏,日头毒得能晒化地皮,知了在树上叫得人烦。我才几岁,赤着脚跳进渠沟玩水,脚底被玻璃碴划了道口子,血顺着脚缝往下滴,我咧着嘴哭,往家跑。爸妈在田里干活,是奶奶迎出来的。她一边用布给我裹伤口,一边数落:“野小子!该!” 语气凶,手却轻。后来上高中,右脚底长了肉刺,疼得走不了路,休学在家时才想起,许是那时留的根。
老家的医疗差,只能请 “赤脚医生”。方医生住得近,背着个红十字药箱,里头装着听诊器和药。他看我脚底的脓包,说要割。没麻药 —— 那时麻药是金贵东西,轮不到我们。几个大人按住我,他拿手术刀划下去时,我哭得能掀了屋顶,嘴里胡骂着,最后疼得快晕过去。后来走路久了,那地方总像要裂似的,可比起奶奶给我裹伤口时的手温,倒也不算什么了。
小学时的一天,有人跑到学校喊:“你奶奶快不行了,快回家!” 我懵懵懂懂跟着跑回家,奶奶躺在床上,眼闭着,气若游丝。我走到床边,她忽然睁开眼,一把攥住我的手,攥得紧。我吓得哇哇哭,没一会儿,她的手就松了。
第二天我就病了,发烧,昏昏沉沉。家里人说,是被奶奶 “惊” 着了。奶奶出殡那天,他们把我抬着,从灵柩上绕了一圈。奇了,第二天烧就退了,没吃药没打针。我到学校跟同学说,有人告到老师那,说我讲迷信。那时候风声紧,老师把我训了顿,我就把这事咽进了肚子。
如今奶奶早不在了,可她解裹脚布时的样子,攥着我手时的力气,还在心里晃。愿她在那边,脚能舒舒展展的,不用再裹着布了。
父母:岁月里的疼与愧
我们家原是九口人 —— 爸妈,我们姊妹七个。可母亲说,我上面原还有个哥哥,冬天里被被子捂没了,埋在屋后的小坡上,连张照片都没留。
总疑惑父亲怎么娶到母亲的。父亲是贫农家的娃,瘦,身高刚过一米七;母亲是地主家的女儿,一米六八的个子,站在那,比父亲还显挺拔。那会儿刚解放,成分是天,农民躲着地主走,我后来申请入团,还得写保证 “不跟外婆家来往”。可他们就成了家,生了我们七个。
父亲年轻时是生产队的会计,账算得清,大队里的机器坏了,他也能捣鼓好。有回他在大队部修机器,顺手给我做了辆带轮子的小车,木头削的,刷了点漆,我没等做好就天天去瞅,结果不知被谁拿了,心疼了好久。
他还唱过戏。有年大队部礼堂演《智取威虎山》,他扮杨子荣,穿件里子带毛的军大衣,戴顶毛边帽,手里甩着马鞭,踩着锣鼓点在台上走,英气得很。大伯家的大姐说,他总把我带在身边,有回我在舞台角落睡着了,口水淌在他的戏服上,他也不恼。后来我上学爱唱歌,许是他给的底子。
可父亲命苦。二十年前查出喉癌,手术后熬了几年,还是走了。他烟瘾大,一天一包,“大前门”“白板”,啥烟都抽。母亲跟他吵,他总说 “解乏”,戒不了。后来病发时,我在新疆喀什,接到消息就往回赶,等到了家,兄弟姊妹已把他接到江苏二妹家,要去南京看病。我托了同学,把他送进南京煤矿医院做了手术,医生说要化疗、复查,可我回了新疆,家里没人领他去,就这么拖着。
他走时,我没赶上。2002 年的事,刀郎那首第一场雪的歌还没出来。我从喀什坐火车到武汉,急着回家,在武汉花八百块钱包了辆出租车,说好连夜送我回安徽望江。可刚过武汉长江大桥,司机就把我转给一个大货车司机,说 “他送你到安徽”。我不情愿,可他带了两个壮汉,我只能认了。后来问货车司机,才知对方只给了几十块 —— 那时候八百块,够家里过好一阵子了。
半夜,货车司机把我扔在望江境内的高速上。四周黑黢黢的,路两边是树林,风一吹,叶子沙沙响,像有人走动。手机没电了,我摸着黑往前走,心里发慌,又念着父亲,一遍遍想 “大大(老家称父亲的土话),等我”。走了不知多久,见着个加油站,才敢停下来,蹲在屋檐下等天亮。
到家时,母亲红着眼说:“你大大临走前一直睁着眼,等你。我看他熬得苦,说‘撑不住就走吧’,他才闭了眼。” 我望着父亲的遗像,眼泪止不住地流 —— 他是不是有话跟我说?是不是怪我没早点回?子欲养而亲不待,原来不是句空话,是剜心的疼。
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守着老房子。那是父亲在世时盖的两层小楼,如今漏雨了,墙皮掉了,母亲一个人爬梯子修,摔倒了也没人扶,只能喊隔壁邻居。后来我们商量,让弟弟把她接到江苏。
如今母亲八十六岁了,虚岁八十七。眼睛花了,耳朵背了,糖尿病、高血压跟着,身体一天比一天弱。可我总想起她年轻时的样子 —— 村里人都叫她 “四姐”,插秧割稻,挑水浇地,风里来雨里去,把七个儿女拉扯大。她那时腰杆直,说话响,谁能想到,如今会蜷在椅子上,说 “房子里有鬼” 呢?
去年姊妹们商量,每家轮着照顾一个月,远的出钱。从大姐开始,她身体不好,糖尿病比我重,可还是尽心。轮到大妹,她在上海,既不接老娘过去也不付钱,还把我们姊妹电话拉黑了。我看着弟弟发来的视频,母亲坐在椅子上,眼神空茫,心里又酸又涩 —— 这还是那个 “四姐” 吗?只盼老天多留她些日子,让我还有机会,多喊几声 “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