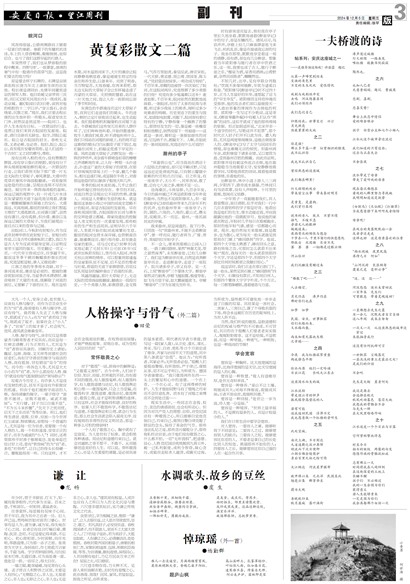皖河口
风刮得很猛,公路两侧路肩上铺着一层素白的寒霜。寒霜下的车辙坑坑洼洼,车上的人昏昏糊糊,颠颠倒倒,前仰后合。也亏了我们这群早起的行路人。
车突然停了,我们也从梦游般的旅程中醒来。四野空旷,一派萧瑟,凛冽的寒气中有一股清冷的蒿草气息。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
原是要去怀宁石牌的。石牌是京剧鼻祖程长庚当年北上演剧生涯的出发地。程长庚是清同治、光绪年间徽班进京的领军人物。他自幼被父亲带到三庆班,而以《文昭关》《战长沙》一战成名,轰动京城。翻《梨园旧话》旧册,读到对他的唱腔的十二字以评:“穿云裂石,余音绕梁,沉雄之致。”现在,我们正要去程长庚的出生地补拍一些镜头,取道安庆北门外,居然误走到这里——皖河口。也许人生本没有目标。一次错误的行走,竟然让我们来到古皖国的发源地。皖者,清白完备而无缺也。皖字,因皖公起名。皖公是古皖国的君主。春秋无义战,义者必稀,也必贵。皖伯,皖公,皖公山,直至现在安徽省简称,是人们送给一个古时仁义之君的雅号,尊称。
没有出将入相的戏台,没有铿锵的锣鼓,没有穿云裂石的唱腔,更没有台下伸头缩颈如痴如醉的观众,一次错误的行走,让我们看到天际下那广漠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寒风萧瑟,大漠中的荒草在寒风中海浪般翻涌,一直衔接到远处隐约的山脉,呈现出连绵不尽的灰褐色。隔空传来一阵阵海涛般的轰响,深远辽阔的视野中,有一片或几片水洼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晶亮地呈现着,就像是一颗颗被镶嵌在幕墙上的宝石。大漠高远,天高地阔,眼前的景致让我们想起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虽然没有落日,没有孤烟,但沙漠、滩涂以及深远辽阔的大草甸子,为我们展现出一派亘古以来的苍莽与辽阔。
出皖河口,今枞阳有射蛟台,传为汉武帝封禅毕曾在此射蛟于江。射蛟台的传说,以及古传《盛唐枞阳之歌》,我以为是古人专为汉武帝量身定制,以证明汉室帝王基因的强大。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一代代帝王皆成过往,往事越千年,眼前这冬季干涸而蜿蜒曲折细长的河流,究竟是蛇是蛟,谁人又能说清?
江淮之地的冬季雨水奇缺,对于一条河流来说,滩涂是必须的。宽阔的滩涂犹如河流之母,当夏季洪水肆虐时,滩涂吸纳了大量的水流,既解除了河流的困厄,又缓解了下游的压力。现在是枯水期,河水退到河床下,大片的滩涂让皖河静静地栖息着,像是刚刚生育过的母亲在将养生息,以备来年。而到了明春,当万物复苏,大地春暖,你再来看吧,那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会让你怀疑走进了内蒙的大草原。天照例阴翳着,站在这一片天地之间,竟让人在一刹那间忘却了季节和时间。
灰黄色的牛群淹没在这片大草甸子里,直到它们走进我们的镜头。牛的进入,顿时让这片景致活泛起来,也生动起来。我们提着相机和摄像机往河堤下走去。牛群被我们这些突兀而来的人群吓坏了,它们哞哞地叫着,开始四散逃窜。牧牛人朝我们吼着,听不清他叫些什么,我们只得站在河堤的斜坡上,有的则不忍这难得的镜头白白从眼皮子底下划过,他们躺在河坝上,拍摄这荒漠下罕见的一幕。风吹动着大草甸子,四野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呼声,夹杂着牛群啃食枯草的嚓嚓之声清晰地传来,让人有一种想一头扑进去,扑进这广袤的大草甸子的欲望,在那片厚绒绒的草场上打一个滚,翻几个跟头,相互追逐打闹,或是骑在牛背上,对着那远处隐约的山脉孩子般地大叫几声。
冬季的皖河水流枯竭,几乎让我们开始怀疑它曾经的存在。季节的不同,河流自然会呈现出它不同的性格,就像人。河流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根本。就是眼前这条细小得让中国的河流史忽略不计的皖河,却是古皖国的发源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皖国即在长河与潜水的交界处建立都城。薛家岗遗址的挖掘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次重要发现,那些粗劣的生产和生活用具,证明早在六千年前,人类就开始在皖河流域繁衍生息。眼前的皖河也曾水深岸阔,也曾烟波浩淼,能灌溉良田,能行得舟船,甚至能走皇家的船队。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真实地记载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出枞阳至皖口,登舟而入皖河,再登天柱山封禅的情形。可以想象到那逶迤的皇家船队前不见尾、后不见首的整肃与壮观,碧蓝的天底下彩旗猎猎,宫廷仪仗队用复杂的编钟奏出了浩荡的乐曲。
风越刮越猛,那片大草甸子上,无边无际的荒草海浪般翻滚,翻涌出一段段历史,一个个英雄人物,彩旗猎猎,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曹孟德、周公瑾、曾国荃、陈玉成,“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百年来,浓稠的血液曾一次次染红了皖河,在这皖河两岸,究竟埋葬了多少英雄的白骨?究竟有多少冤魂难以还乡?逝者如斯,千百年来,皖河依然在默默地流淌着,一条皖河,经历了太多的征战与杀戮,听过多少战场上的厮杀,闻听过多少死难者的呜咽。历史更迭下的重生与毁灭,如雷如电如雾,而眼下,皖河却有着它特有的宁静,宁静得像一个睡熟了的婴儿,那曾经发生的一切,像是被一块橡皮轻轻地擦过,居然没留下一丝痕迹——这就是一条河,哪怕是一条细如游丝的河流,它包纳千古,都摄天下。人啊,在如此的一条河流面前,究竟还有什么可说的?
滁州的亭子
“环滁皆山也”,而当我站在酒店十六层临北的窗前,却只见平畴沃野,只见远远近近处清流四溢,只有烟云朦胧中依稀的村庄和点点白屋。目之所及,有一座座亭子,大小不一,其形各异,数了数,总有七八座之多,唯独不见一山。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九百余年矣,今日的滁州城已不再是欧阳修当年外放的滁州,当然也不见欧阳修其人,但一篇《醉翁亭记》却给滁州带来九百余年不朽的名声,也给滁州带来一座座亭子:方的,圆的,六角的,八角的,歇山式,攒尖顶,庑殿顶,不一而足。滁州,一座名副其实的亭城。
我来滁州,原是闲逸的。放下行李,只因我一句“到滁州来,不能不去看醉翁亭”,便一呼而应,随行者界为、广缘、常舟、常福四位年轻学子。
不一会儿,便来到琅琊山公园入口处。一路上峰回路转,果然“林壑尤美,望之蔚然深秀”,未至醉翁处,已有几分醉了。我们是为醉翁亭而来,自然是直奔醉翁亭而去。走进醉翁亭,走进了一座院子。院内诸多亭子,亭又有亭。见一大石,上刻“醉翁亭”三个篆体大字。醉翁亭果然灵巧娟秀,亭檐飞翘如翼,极度夸张,如飞鸟方息于泉,如大鹏展翅欲飞。亭额“醉翁亭”三字为东坡先生所书。
时有游客进而复去,独有我在亭子里长久地坐着,默默地诵着《醉翁亭记》中的句子,却是东鳞西爪。清风习习,鸟语声声,亭檐上有几只麻雀肆意地飞来飞去,叽叽乱语,像是在接诵我忘却的句子。我坐在那里,默默地享受着这一刻的清静,没有酒,却也有几分醉意。想象着当年欧阳修与随行者在亭中饮酒之乐,这一刻,我便也成了古人,随行于醉翁之乐,“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醺醺然也。
不知几时,出亭,见有亭联分列抱柱:“饮既不多缘何能醉,年犹为逮奚自称翁。”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不过四十岁,正当人生最好的年华,遂想起了岳飞的“早生华发”。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而受排挤,他的攻击者们却以最能毁灭一个人政治形象的绯闻作为击倒他的利箭。欧阳修一生写过不少艳词,这是事实,《醉翁琴趣外编》中有被人们认作“浑亵”的词作,这似乎就成了他的那些绯闻的依据。但正如胡适所说,“北宋并非一个道学的时代,写艳词并不犯禁”,那个时代正人君子们并不以此为讳。遭人构陷,尤其是两度绯闻缠身,是能击倒很多人的。《醉翁亭记》写了太守与民同乐的情境,却也难掩无言的烦忧。但滁州两年余,欧阳修留下诸多业绩,又以宽简为政,受到滁州百姓的拥戴。由此而证明,欧阳修并没有被这些流言击倒,他在滁州稳稳当当地做着太守,安安静静地做着学问,写着他喜欢的诗词,做着他该做的事情,乐着他的乐。
出醉翁亭,林中小道上游人三三两两,夕阳西下,路旁流水潺潺,竹林间只有鸟语欢歌,没有人声喧哗。十月里的琅琊,悠闲而又恬静。
一中年男子一直跟随着我们,其人着装整洁,面目清朗,似乎对我们一行中几位衣着别样的学子很是好奇。他看出我是他们的先生,便主动接近我,并向我敞露出他的一段蹉跎岁月。他说他的家就在附近,年轻时几乎每日在琅琊跑步,那时的他年轻气盛,感觉一切都随心而欲。现在,他仍然每天来琅琊,既是散步,也为散心,更为每天一抬头就能见到那刻在门额上“峰回路转”四字。他说,那四个大字他太熟悉了,峰有回头之意,路有转角之功,可那时怎么就看不出来呢?“现在,我每天仍一抬头就看到那四个大字,字还是那四个字,但那四个大字却比任何时候都更让我触目惊心。”
说这话时,我们正走在那石拱门下,猛一抬头,果然见到石额上“峰回路转”四个大字。石额没有款识,不知刻自何人,但那四个繁体大字字字朴直,个个方正,每一刀都笔锋硬朗,透着刚劲与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