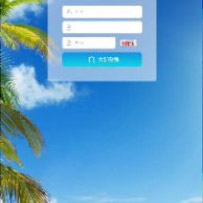夜的脚步轻得像沾了露水的棉絮,悄没声儿漫过青砖院墙。案头那盏青瓷小灯捻灭时,月光正顺着窗纱的细格爬进来,像极了旧时女子绣鞋上垂落的银线,轻轻漫过床沿的竹席。指尖拂过枕边码得齐整的书册,粗糙纸页裹着旧年的墨香,忽然记起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写的:“读书如游山,触目皆可悦。无需结伴行,孤往亦自得。”可不是么,这枕侧的书、窗间的月,原是比故友更懂人心的伴。
那本《稼轩长短句》,书脊已被摩挲得泛出浅褐,扉页边角还留着去年秋夜摘录的短句:“幼安的豪情,是埋在剑鞘里的星子,藏着风霜,却亮得灼人。”今夜随手一翻,恰好停在“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页脚,抬头便见月光斜斜搭在竹帘上,竹影疏疏落落落在书页间,倒像是给那些词句镶了圈细碎的银边。忽觉千年前的某个夏夜,辛弃疾大抵也是这样倚窗而坐,看月光漫过案头剑穗,把满腔壮志细细融进词里,连墨痕都带着剑气的清刚。
一本发黄的《东京梦华录》,夹着我数前年写的一页读后感,今天读起来,还感觉有点意思。那日雨落得细碎,夹在“州桥夜市”那一篇,就为着孟元老笔下“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的鲜活。此刻月光落在海棠干上,花瓣虽失了往日的嫣红,却仍留着淡淡的甜香,混着书页里散出的旧墨味,竟让人恍惚见着汴河岸边的灯笼,在暮色里次第亮起,叫卖声、笑语声顺着水波漫过来。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这般沉浸于旧时光的“沉醉”?大多时候都在俗事里奔忙,倒是这半床书,能偶尔把人拉回那样鲜活热闹的岁月里。
著名文化名人、我的老师汪海潮曾说过:“读书要趁夜,就像品茗要趁闲。”汪老师1982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文采飞扬,当年他的作品就入选《全国大学生作品选》。所以我想最好的读书时光,原是在这样万籁俱寂的深夜。没有街头小贩的吆喝,没有邻居家孩童的嬉闹,只有月光从窗缝里溜进来,轻轻落在书页上。读到会心处,便摸出钢笔在页边写几句感想;读到眼皮发沉时,便把书往枕旁一放,头刚挨着枕头,就被满床月色紧紧裹住,连梦都沾着铅墨的书香。
窗外的月光又浓了些,照得屋里的木桌、竹椅都蒙着层碎银。我把《稼轩长短句》轻轻合起,书香与月光混在一起,竟比被窝还暖。看到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刻若有故人坐在对面的竹椅上,想必也会和我一样,捧着热茶对着满床月色与书香,不必多言,只凭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这般静谧,原是比千言万语更贴心的慰藉。
其实人生所求,不过是这样的寻常夜晚:小窗漏进半床月色,枕侧堆着几本闲书。不必求什么轰轰烈烈,只需在这样的夜里,指尖拂过书页时能触到旧年的温度,抬头望月光时能想起某句诗,便已是岁月最好的模样。就像院角那丛竹,年年春日都悄悄抽芽,不声不响,却把绿意漫进每个路过人的心里。
柿红染透故园秋
暮秋的风掠过窗棂时,总带着几分清冽的凉意,我习惯性地朝楼下望去。小区花园里的那棵柿子树,此刻正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像无数团燃烧的小火球,在澄澈的蓝天下格外惹眼。阳光穿过枝桠,落在橙红的柿果上,漾开一层柔和的光晕,连风里都似掺了丝清甜。唐代刘禹锡的诗句:“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本因遗采掇,翻自保天年。”诗中勾勒的柿果挂枝之景,穿越千年的时光,与眼前的画面重叠,竟毫无违和。原来早在千年之前,这寻常的柿果,就已入了诗人的眼,成了时光里耐人寻味的景致。
老家的院落前,也曾有这样一棵柿子树,是奶奶在我幼小时亲手栽下的。如今想起,那树仿佛是伴着我长大的。我从蹒跚学步的孩童长成挺拔的少年,它也从纤细的树苗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记忆里,每到深秋,那树柿子便成了小院最鲜亮的风景。青灰色的院墙围着矮矮的土屋,墙根下还种着几株月季,而虬曲的柿树枝桠从院角伸展开来,挂满了橙红的果实,远远望去,像给古朴的小院披了件喜庆的红绸衣,连带着整个村子都多了几分烟火气。
那时乡下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棵柿子树。老人们常说:“宅前有柿,万事如意。” 这朴素的期盼里,藏着对生活最真挚的向往。柿子树不挑土壤,耐旱耐贫瘠,种下后只需偶尔浇浇水、松松土,便能年年挂果。而且它的果实耐储存,哪怕到了寒冬,把柿子埋在麦糠里,想吃时掏出来,依旧清甜爽口。
幼时的我总觉得这柿子树性子太慢。开春时,院外的桃树、杏树早早绽了满枝粉白,引得蜜蜂嗡嗡绕枝,它才慢悠悠地冒出几片嫩黄的芽尖,像是还没睡醒;夏日里,村头的樱桃、李子都已缀满枝头,孩子们挎着小篮在树下争抢,它才悄悄开出细碎的淡黄色小花,藏在绿叶间,不仔细瞧根本发现不了,只有凑近了,才能闻到一丝淡淡的清香;直到初秋,邻院的梨子、苹果都陆续摘完了,晒满了屋檐下的竹匾,它枝头上的柿子还裹着青绿色的外衣,透着股不慌不忙的劲儿。
我常蹲在树下,托着腮抱怨:“这树怎么这么慢呀?啥时候才能吃柿子哟?”奶奶总会放下手里的针线,擦了擦手上的线头,笑着摸摸我的头,轻声说:“傻孩子,万物生长都有自己的时辰。你看那麦子,要经冬雪覆盖、春雨滋润,才能在夏天灌浆饱满;这柿子也一样,得等秋风吹、霜雪打,把涩味都逼走,才能变得香甜。做人也一样,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稳扎稳打,才能活出滋味。” 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只盼着柿子能快点成熟,却不知奶奶的话里,藏着一辈子的生活智慧。
可我哪懂什么时辰,满心思都盼着柿子快点成熟。有一回,见枝头上几颗柿子微微泛了红,像小姑娘害羞的脸蛋,我便偷偷搬来小板凳,踮着脚摘了一颗。刚咬下一口,涩味便直冲喉咙,像吞了口黄连,我慌忙吐了出来,皱着眉直跺脚,眼泪都快憋出来了。奶奶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瞧见我这模样,笑得眼角堆起皱纹,眼角的细纹里都藏着温柔:“‘霜降到,柿子俏’,这是老辈传下的理儿。没经霜打的柿子,就像没经世事的孩子,哪能不涩呢?”
从那以后,我便天天盼着霜降。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院子里看柿子,盼着它们能快点变红。终于等来了霜降时节,一夜霜露过后,满树的柿子像被施了魔法,全都染上了酡红,有的还带着几分橘黄,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柿果上挂着晶莹的霜花,轻轻一碰,霜花便簌簌落下,沾在指尖,凉丝丝的。我搬来梯子,在奶奶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爬上树,摘下一颗熟透的柿子,剥去薄薄的果皮,咬一口,清甜的汁水在舌尖散开,那股甜劲儿,顺着喉咙一直甜到心里,连眉眼都染上了笑意。
汪曾祺说过:“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如今日子好了,超市里的水果一年四季都不断,桃子、橘子、葡萄,想吃什么随时都能买到,我却没吃过当年老家那样甜的柿子,也再看不到奶奶的身影了。可有些味道,早已不是单纯的味觉记忆,而是藏着岁月的温度,刻着亲人的牵挂,再也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