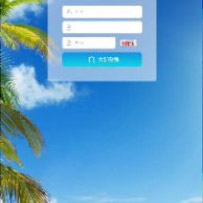时间从来不语,时间也从来不恋,它如白驹过隙,悄悄春去夏来,秋去冬临,又结下一些伤疤,在心里升腾起丝丝烟雾,这烟雾一直笼罩心房,总有解不开的结和往事……让我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就跪念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母亲成了一个孤独的人,我则变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孤独人。其实,这些年来,只要停下来静下来,我就会想起父亲,想起他生前的点点滴滴,想起他和我们一大家子在一起的艰苦岁月……
父亲是一个农民,但他从来不干农活,哪怕就是最忙的双抢,他也从不割一稞稻谷或插一根秧苗。每年到农忙季节,家里总会来一些陌生的叔叔阿姨帮我们干农活,父亲说,他是巧干。原来,父亲用他的牛儿门去帮他们家犁田,然后换来一些廉价的劳动力完成我们家插秧或割稻…我不得不承认父亲为人处世聪明过人,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从来没有干过农民的活,插田割稻都是母亲或请一些人来劳作 ,哥哥大点,就跟在母亲后面学着种田挑粪之类的活,集中的农活,一定要等到星期天,我们兄妹几个放假了就分工协作帮忙干,而父亲自己清早就去买些鱼肉犒劳我们,当然也不忘记给自己来一瓶华阳大曲和一包蝴蝶泉的香烟。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里因为缺人看牛就歇学了。父亲是一个牛贩子,家里常常牛儿成群,正因为有许多的牛儿,就需要有小伙伴看牛,那时候一个人要看好几头牛 ,而我们家的牛基本都是散养,我们清早赶到山上,然后就把牛儿散开,随它们自由吃草喝水,相互嬉闹,而我们自己则到处觅食打野,傍晚回家又赶牛回栏,结束一天的野外生活…现在想来,放牛的日子很快乐,也很童趣,但我那时候并不满足放牛就是自己的生活,偏偏想去学校读书,看见同龄人去学校上学,心里就羡慕的不得了,有时候流露出想念书的面容,祖母看出我的心思痛在眼里,用纺纱织布的钱给我买画报和小人书,这样我放牛就带着这些书籍去看,一边放牛一边看书识字学写文章,这也为我现在的写作奠定了一些坚实的基础。后来有一个机会,古城小学来了一个姓常的老师,应该是某师范毕业就分配到了我所在大队古城小学任教,常老师是一个教育水平和技能都很高的老师,那一年大队扫盲,我再一次踏上入学的门,因为有了放牛的经历,所以读书就格外努力,常老师认真执教,我认真苦读,因为放牛丢了一年的功课,不但要把以前没读的补读,还要研读现在的新知识,所以我那时候语文数学都是班级第一 ,后来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我大概是全乡的第一名,当然并列的有一个名叫张辉的同学,都是以满分的成绩进了武昌中学。父亲再也没有要我歇学看牛了,因为我的成绩好 ,我那时候也成为了同龄人中第一个读书的女孩。我依然记得我那时候的装扮,黄色的军服,蓝色的卡其裤子,短短的头发,扮相上就是一个俊美的少年男孩。我那时候读书要感谢祖母的创新思路和父亲的不偏见,我一个农村的女孩,能够读书就是很荣幸了,那时候家里一些亲戚都劝父亲不要让我读书,说女孩子读什么书,以后是别人家人,让她做裁缝打工还能赚钱补贴家用,但父亲这一次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一直供我读书求学,直到卖掉了家里的一头黄牛……
父亲是一个贩牛的,所谓贩牛就是将别人家的牛买回来在家看一段日子再卖出去 (可能是卖给牛贩子,也可能是卖给庄户),中间赚一些交易费来渡荒年。父亲怎么成了牛贩子,那时候牛贩子基本上被认为是好吃懒做的人所干的事。说起父亲从事贩牛也是生活所迫,听母亲说早期的父亲因为长的高大帅气被大队推荐当兵,好像是武警吧,但祖母死活不答应,理由是父亲只有一个人,去当兵了就回不来,家里没有劳力也没人养祖母的老。一九七七年,父亲患了胸腺瘤在上海某医院做了手术,术后的父亲身体柔弱,没有一点免疫力,更不能干农活,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跟了邻村的大爷学贩牛,贩牛不需要出力,只需要牵着牛鼻子,懂牛的性情和价钱就行了,父亲对贩牛很感兴趣,他不但能用手摸牛嘴里的牙齿而不被牛咬伤,还能用眼称出牛的重量 这也是贩牛要具备的技术,后来的父亲一直靠贩牛来养家糊口,所以牛在我们家里成了必不可少的伙伴。至于弟弟为什么取名“开流”,也是因为那一年父亲做了手术,家里又多了一口吃饭的,家里开支各方面要“开源节流”的缘故吧。
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惯养我们的坏脾气和坏习惯。也经常教育我们勤以修身俭以养德。有一次我因为不懂事撕了父亲贩牛用的二联发票,被父亲狠狠盯了一个棒力子。父亲因为牛生意做的好,也善结人缘,那些天南地北的牛贩子,在我家可以随便吃饭住宿,有时候常常是母亲做了一顿饭菜来了一班贩牛的师傅又不得不再煮饭菜,父亲说出门人不容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家里来了朋友一定要管他们吃好睡好,所以我们家那时候就置办了客床,供外地来的贩牛人住宿用。父亲说出门人不容易,你善待了他人,他人必然善待与你,在一起都是缘份,在一起要相互照应。我记得上初一放寒假,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到江心洲贩牛,那户住在江心洲的伯父,煮了好多好吃的美食给我们,还带我们到安庆玩了一天。
父亲患病五年,期间的住院治疗都是母亲陪着他,我最后一个陪父亲是2011年岁末。那年的十月下旬我从雷池赶回家看望双亲,母亲告诉我父亲两腿无力,也没有什么食欲,我打电话告诉大哥,要求带父亲去做个检查,第二天我们带父亲去县医院骨科,以为双腿无力是骨科的事,医生开了磁共振检查,报告结果是腰椎盘突出,于是就带父亲回家休养,谁知此后父亲再也没有站起来,卧床两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现在想来应该疾病复发了,父亲去的那两个月,我请假在家侍候,母亲把家里的母鸡都杀了炖汤给父亲喝,开始父亲还能整碗地喝,后来不愿意喝了,鸡肉也吞不下去,但他在睡梦中呢喃着“吃饭喝酒”,又在恍惚中呼唤已故祖母的名字…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十二年了,十二年里,我无时无刻不想念父亲,有一次下班途中看见一个穿中山装的老人在前面走,我以为是父亲,那身形那背影多么酷似我的老父亲呀,我甚至快走几步跑上前看看是不是父亲,然那陌生老人给了我一个错觉和幻觉,明明知道不是我慈祥的父亲偏偏还要执念跑过去验证一下,这或许是思念父亲心切情切吧。回忆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时光,还有老屋流淌的少年情怀,以及一群缺鼻子牛儿,那些泛黄的日子充满色彩、纯朴和敦厚,也织了一张解不开的网,这网一直网住了童年少年青年和现在中年的我,我情愿在这网里游弋挣扎回忆书写,这或许就是父亲留给我的散文,也是父亲留下来的散文诗,更是父亲母亲温暖我的襁褓 ,愿父亲在天堂安好,愿梦里多一些和父亲从前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