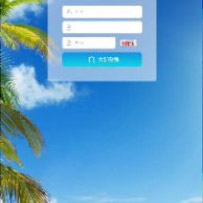另一个世界,訇然打开
这里是泸州老窖的高粱基地。泸州老窖是用一种原料即高粱就能酿出酒,而且是名酒的白酒。此中意味深长:“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就是一。一,不偏,不散,不杂,不变,“故君子执一而不失,人能一则心纯正,其气专精也。人贵取其一,至精、至专、至纯,大道成矣。此自然界生产力之不二法则。”《老子》因此断言“: 抱一而天下式。”
泸州老窖只用“一”酿成,可能只是偶合,但偶合比刻意更合乎道,更能接近道。道可道,非常道。泸州老窖这酒,亦非常酒。道是说不清的, 酒也是难以说清的。它是一种饮料,但又绝非可以只视为饮料。它不是生命所必需,却又是生命乃至精神所必需。在中国,从上古开始,它就获得了仪式性质,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得兼而不悖。自古相传的俗语“无酒不成席”,强调的就是有了酒才不是一次平常的吃饭,而是一次仪式。并且,也是从中国文化滋生开始,酒就浸润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与中国文学艺术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是以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人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乃至出现了“诗酒风流”这样一个千古流传的成语。现存史料中,泸州向周王朝交纳的贡品有泸州所产“巴乡清”酒,泸州人、周宣王重臣尹吉甫在《诗经·大雅》中所述“显父饯之,清酒百壶”,是关于泸州美酒的最早记载。也就是说,最迟在周代,泸州的酒就已经全国性地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了。周代就能酿出这样的酒,泸州老窖的出现就是必然。
我最早品尝到泸州老窖,是在 1985 年的兰州。甘肃省作协和《飞天》杂志社主办的一个小说笔会,两位藏族作家不喝水,军大衣口袋里每天揣着一瓶泸州大曲。第二天晚上,其中一位来请我去他们房间坐坐。我一进门,另一位就迎上来递给我一瓶泸州大曲,他们自己当然也是一人一瓶,豪爽地说:咱们都把这瓶酒干了!酒量只有一两的我怎么解释都不行,他们就一个理由:这么好的酒,怎能不喝一瓶!
我由此记住了泸州老窖:窖香浓郁,清洌甘爽,回味悠长。后来当然又多次喝过,大多是和诗人们一起喝,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全国性的诗歌笔会,来宾中,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韩作荣和我应邀做了一个诗歌讲座。我的讲座讲过的那天晚上,有人来到我的房间里来要和我喝一瓶, 竟然也是两瓶泸州老窖,而这位来客是笔会的司机,一个中年男人。他说:“旁听了你的讲座,不懂。但感觉是今儿晚上咱俩一定要喝一次酒!”
我一愣后真的有些激动——这是怎样的一种诗酒风流啊!绝对无法事先想象或虚构。而他听了诗歌讲座后买来的酒,为什么是泸州老窖?或许他本就喜爱这酒,或者就只能说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了。
我那次讲座的题目是《形而上学·符号·零度》。讲的既是诗学,也是哲学。它们需要突破自我形体的形而上。酒也一样,它是有形的物质, 但在中国文化中,它的本质是超越形体的,也是形而上的。学术界借用西方的“酒神精神”,认为中国也有酒神精神。其实,就像这个酒与那个酒不是一回事一样,中国“神仙”这个词中,神与仙不是一回事。比如说, 土地也是神,但它不是仙。中国所有的,不是类似于西方的那个以生命力冲破理想束缚后的感性解放为内涵的酒神精神,而是酒仙精神。仙者,仙风道骨。仙风道骨是什么?是飘逸,没有形体约束的飘逸。
酒仙精神就是酒赋予的飘逸精神。这飘逸的核心依托是道,也就是老庄尤其是庄子哲学:通过坐忘、心斋,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生死齐一, 获得的精神的自由状态。而西方通过酒获得的感性解放仍然是肉体的——感性总是肉体的感性,没有肉体就没有感性可言了。
老庄是中国历代文人的灵魂,但是,坐忘、心斋比较难,坐在那里就真的能忘记物质世界的一切和自己的肉身?用心“吃”斋就真的能百欲皆空物我同一?难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们(那时的官员也大多都是文人) 终于发现了一个捷径:酒可以取代坐忘和心斋,使自己进入物我、天人合一、生死齐一的精神自由状态。于是,酒仙精神渐渐形成,酒就从一般饮料上升成了文化。至于各等庶民,历来是受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所化,因此,虽然不是很知其所以然,也有意无意地追随酒仙精神或者说酒文化, 欣赏饮酒所获得的飘飘然了。
不禁想起了泸州老窖的主题词“: 天地同酿,人间共生。”它的内涵,包括我上面所述——泸州老窖,最明确地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内涵的酒。
在泸州老窖窖池,我再次感受到了笼罩天地的高粱的那种沉肃。这些现在时的高粱,奇妙地在一个个 1573 年的窖池中发酵,我能看到的,是封住高粱的 1573 年的窖泥。湿润的,闪耀着泥土的光泽。酒气,无处不在地悄然蒸腾、缭绕。1573,2016,几百年的时光啊,继续在酿着这酒。我下意识地几乎不敢说话。天地同酿,人间共生的时刻,人应该低下头去,与正在转变为酒的高粱,以及这仍然活着的 1573 年的窖泥一起沉肃。
据主人告知,高粱、小麦等等是在发酵中先变成糖,然后由糖再变化为酒。糖和酒竟然有这样的关系,匪夷所思的又一个秘密。人,不过是各种秘密中活着,饮下这酒,其实是饮下了秘密之果。
走出窖池,染上酒香的微风荡漾,想起了据说是胡耀邦在泸州饮过泸州老窖后写下的一句题词“ 风过泸州带酒香”,想起据说写于泸州的《三国演义》卷首词“一壶浊酒喜相逢”。风过泸州带酒香的酒应该清清亮亮,一壶浊酒喜相逢明确地说了酒是浑浊的。那么,清澈透亮的泸州老窖能否也说成是“ 浊酒”? 可以。酒之清,之浊,其实不在酒而在饮者。泸州老窖,清浊咸宜。
入夜时分,天气预报无雨的泸州,忽然降下一场急雨,我们一行正在城墙边泊着的酒船上饮用泸州老窖,绵绵酒香飘入长江的雨和波涛,那不可能返回的真实里,而另一个世界,已经被入腹的泸州老窖訇然打开......
三河水声
所有的泥土里都栖居着水声,三河更是如此。
三条河,丰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从大别山汹涌奔流而来,在此穿镇而过而合流,带来并且产生了更多、更澎湃的水声。
大别山奔流而来的水和水声,带着石头。
渔民出身的我,对水和水声有着特殊的亲近感,我熟悉河流的白天与夜晚,并且深知观看河流的最好时分是暮晚。那时,河流逐渐从白昼进入夜晚,河水变幻着,在最后的天光消失之际,开始发出它自己的光……
没想到的是,我看见三河的水,听到三河的水声,是因为刘铭传——参加“海峡两岸(合肥)纪念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诞辰180周年”的活动。 但我对刘铭传并无研究,我实际参加的是这个纪念活动中的一项:两岸文学交流。刘铭传,两岸、文学、三河,互不关联的事物,突然显示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紧密的逻辑联系。
万事万物都是如此?
与此相比,到达肥西三河居然正好是黄昏时分就只是一个平常的巧合了。
是一个下着若有若无细雨的黄昏,穿行于三河古镇的街道,渐渐就走进了灯光与夜,不经意间就遇到一座桥,看到桥下的河水。只是这水极其明亮,甚至可以说是繁华的、现代的灯光照亮的河水,并不能看到河水自己的光——河水五彩缤纷而闪烁,仿佛并非来自映照,而是水的深处也有无数彩灯,将灯光晃动着照射上来。
曾经多次听诗人刘祖慈先生叙说过他童年时的三河古镇。祖慈先生的叙说,总是与穿镇而过的这三条河密切相关,关键词又多是傍晚或者夜晚。于是,熟悉河流的我在祖慈先生的叙述中,多次下意识地“看见”这三条河,是暮色或者夜色中油灯闪烁的河流,感受到的荡漾在古老街巷中的汩汩水声自然也是昏黄的。
眼前繁华的三河,与祖慈先生回忆的油灯绰约、老屋黑影幢幢的三河,似乎在表明:直接看到的总是现在;回忆中浮现的,都是历史。
三河现在的繁华,大概一半是因为它已成了游客络绎的名胜,一半也与肥西是全国百强县之一,经济实力雄厚有关。肥西素有“淮军故里、改革首县、花木之乡、巢湖明珠”的美誉,是安徽省的经济强县。不然的话,古代因舟楫之便而形成,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弃水路而重陆路交通的当今,早已就颓败得少有人影了。
不变的是水,并且是太多的水,外环两岸、中峙三洲的三河,虽然离江南很远,却具有典型江南小镇风貌。据说镇外也是河网纵横,水气氤氲,长约10公里的湖岸逶迤而去,若是盛夏,有万亩荷花红艳欲燃,芦荡与桃林相望……
第一次来到三河的我,对这种水乡景色并不陌生。让我有些讶异的是我一直以为应该是北方小镇气质粗犷的三河,竟然是极其柔媚的典型的江南水乡,而江南水乡的外貌里面,水和水声中又不仅有石头的声音,还有金戈之声……
很早就从历史书中知道太平军与清军激战过的这个三河古镇。那是怎样惨烈的一场大战啊!1858年11月,一路势如破竹,在九江一举歼灭太平军将领林启容账下1.7万名将士的湘军悍将李续宾,连陷安徽四城之后,率湘军精锐围攻三河。刚刚摧毁清军江北大营的太平天国前军主将陈玉成、后军主将李秀成率军昼夜兼程先后赶到,迂回包围湘军,激战后全歼湘军,包括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
之所以有这样规模的三河之战,当然是因为三河是东镇巢湖、北扼庐州、西卫龙舒、南临浅川的战略要地,对于清军来说,三河既是进攻庐州的必争之地,又是太平天国庐州府和豫东南的粮食,由三河入巢湖下长江供应天京的中转站。
见诸史籍的发生在三河的大战,还有公元前537年吴楚之战,吴胜楚,楚败。吴楚纷争于公元前510年,吴将伍子胥又一次在此击败楚军。三国时曹操、明末张献忠都在此驻军并在巢湖训练水军。
斗转星移,水路已不再重要的现在,三河古镇应该再也不是军事要地,而是一个供人游览、怀古之地了。
据说社会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一件事只有在能被哲学家伊利亚德称为“复现”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不再复现的,就是真正的历史。
三河古镇,虽然成功转型为游览胜地,拥有现代的繁华,但它的身影仍然是历史的身影。没有历史属性的,永远是三河的水乡美景。
整个肥西似乎都是这样,刘铭传故居所在的刘老圩、淮军将领张树声老家张老圩等等,都完全如同江南水乡。
我想,这应该与肥西地处江淮交界处有关:其地有江南般风景,其人则或有江南的文气,或有淮北的彪悍。肥西出过刘铭传、张树声等多位淮军将领及段祺瑞、杨振宁等人,就不是偶然的了。
三河还保存有杨振宁故居。不过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发现我已经不记得那故居的模样了,并且也已经将在镇内穿流的那三条河的名字与对应的河流弄混淆了。其实,当时我就没有弄清楚再次遇到的河流,是刚刚见到过的,还是另外一条。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那么,每次遇到的,都是新的河流吧。
记得清晰的,是回程的事:主人安排我们一行乘船返回,在堤坝上,遇到一位拿着丝网准备下网捕鱼的老人。因为我知道这河与巢湖相通,所以我问:现在这河里的鱼还多吗?老人摇摇头,不多。一般都是小鲹条。
几乎没有鱼的河流,有的只是水了。
在游船上,我凝视灯光与夜色中的河水,即使灯光照亮处,那河水也深不可测。
有波浪,因此肯定有水声,只是河流自己的水声与游船冲开水面的水声,以及游船柴油机的轰鸣声搅在一起,难以分辨而听不真切。
是的,这是新的河流,它早已将石头的声音、金戈的声音都沉下去了。
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新的三河、新的肥西、新的时代。
晚餐是在三河吃的。三河的菜肴多与水有关。例如三河酥鸭、清蒸鲫鱼、银鱼炒蛋、清炒虾仁、蒜苗烧黄鳝、茭瓜肉丝、凉拌花香藕、清蒸桂鱼、鱼头锅、鲶鱼豆腐锅、炖老鸭、炖老鹅,等等。点心也有酥鸭米面。
尼尔·豪威在《第四阶段——对美国的预言》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变化无常而且凸显原始本能的时代里。”用餐时,连我都忘记泥土里栖居着的水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