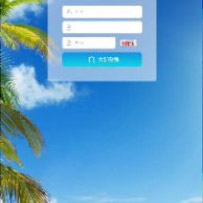车前子的诗歌呈现的是简洁与纷繁之美的两端:要么非常简洁,如格言,如祭祀的密语,充满了令人猜疑的暗示,它是高度提纯和概括的,如《就像最选醒来》、《即兴》系列以及《无诗歌》系列;要么耍弄各种语言的花招,使尽浑身解数,编织语言的宋锦,如《钟表店之歌》《胡桃与独白》《南方与胡同》等作品。最近,他从1978到2016年的诗歌精选集《新骑手与马》正式出版,让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欣赏到车前子诗歌的各种风格。
1
车前子的诗歌是一种突然而起的飞行。这种飞行,没有任何准备动作,要说有的话那他也只是在心中助跑。如同一只苍鹰,“鼓着铅色的风/ 从冰山的峰顶起飞”(昌耀《鹰·雪·牧人》),翅膀上落满大雪,在一片苍茫与空无中,他拖着巨大的阴影滑过祖国的田野。博尔赫斯认为,一个诗人的工作,就是塑造他自己的形象。我看到了车前子御风而行的形象,它的本质是自由,这是他的诗歌的第一个关键词。他享受着自由飞行的快乐——在语言的翅膀上,风送来了水气和远处的河流与村庄的影子。从天而降的阴影,给地上的人带来了不适感。他的散文,是慢慢上升的,从广阔的平原过渡到起伏的丘陵,最后才是莽苍蓊郁的山林。而在他的诗歌中,一步即是悬崖,一步即飞越城市和丛林。在诗歌写作上,车前子是孤独的,也是骄傲的,这是他给自己设定的角色形象:
前卫风度的独角兽,
没有人文关怀。它是兽,
你让它证明什么?
它是独角兽,从黄色的宫殿,
突围,进入;
象牙塔,花梗一样烂掉。
(即兴(独角兽之五))
独角兽,就是天马,天马行空,它是飞行物,在匍匐在地的眼睛看来,它可能还是不明飞行物。“优秀的诗歌,是人类早期暧昧天空中划出的飞行器”,可惜这飞行器如彗星一般几千年才能出现一次。在汉语的诗歌编年史中,二千年前有了绝云气负青天的鲲鱼,水击三千里;一千年前还有神游八极之表的大鹏,簸却沧溟水;而今天只有巢于树上的野鸡,在扑腾中掉落几片羽毛和粉色的诅咒。物种的退化如斯。尽管如此,“诗人(仍然)是一种飞翔的动物,不一定是鸟,……可能是天马。也可能是斗鸡、斗牛——它们都有飞的感觉。或者确切地说,诗人是一种感觉飞翔的动物。”这种飞翔带来的是空前的自由感。艺术精神,说到底就是自由,人通过艺术将自由显形出来。有诗人说:“诗歌就是那把自由和沉默还给人类的东西”,在诗歌的语言积木游戏中,车前子窥见了人生的奥秘,在羁绊环伺的世界里,诗歌是唯一的自由空间。所谓自由,其实就是“落花人独立”,花开花落,但人独立在山巅。在一个合唱的时代甘愿做扣舷独啸的歌者,在众人做同一个梦的时候,只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人睡入
宇宙。
头顶——血
在交配。
(《无诗歌》)
这首诗创造了一种惊异,大生命的惊异。这首诗把生命扩充到天地宇宙那么大,人与宇宙几乎合一,于是便没有了他人他物的立脚之地,他们统统被挤出。“诗歌表达的是我们不可能拥有之物的本质。”车前子决心以高速飞行来把捉,顺便抛洒一些语言在天幕上划过时发出的五颜六色的火花。在他在天梯上自由地垂直上下时,给观看的镜头带来一阵晕眩,不同的水平线带来了逐渐下降的刻度——它最终完成于神像匠人手中。
就像齐奥朗以一生为代价来坚守孤独一样,车前子决心不惜一切来维护这种自由。徐复观说:“文学艺术的高下,决定于作品的格;格的高下决定于作者的心;心的清浊、深浅、广狭决定于其人的学,尤其决定于其人自许自期的立身之地。”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他的牺牲是值得的。
2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车前子几十年的诗歌写作生涯中,他持之以恒地咬牙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努力将自己的诗歌从众人中抽拔出来。不仅是从普通读者,也从诗人中抽拔出来。他几乎是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坚持着一种神秘、私人化的诗歌。神秘是车前子诗歌的另一个关键词。区别于大多数诗人惯于以个性化的方式来表达公共经验和情感,他更多的表达的是私人化的经验。只有当这私人化的尾巴刚好落在阳光下,它才表现出公共性。即使是飞行,他也是隐秘的,拒绝阳光普照和镁光灯,他选择锦衣夜行。关于这一点,车前子自有他的说法,那就是诗歌的“核武器说”:
“诗接近尖端科学尖端科技,就像研究核武器一样,甚至还需要保密。诗可能就是核武器,这更是比喻。反对核扩散,我也反对诗扩散。反对核讹诈,我也反对诗讹诈——比如说什么诗是文学的精华与神的对话宇宙的真理,人类的良知呵灵魂。”
他并不是把诗歌降格,不是的,他只是要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然后,以诗歌本身的名义,去为它赢得荣誉。这是要卸下附加在诗歌上的过多的负载,让诗歌成为诗歌,让骆驼成为骆驼,而不是战略运输工具。他是诗歌秘密的坚定守护者,但这守护的目的却并不在秘密本身,而在于它解密时内外压差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
就像最先醒来
咬出白来,泻入大海的湖水。
咬掉一半,黄色的石窟,兜底
一根绳子用两头回合,撞坏伤口现身说法的
说法。
2000,1,30,午夜
(《就像最先醒来》)
这也许是半睡半醒状态下的混沌潜意识图景,也许是一星半点的感觉纤维摆成的图案。这个梦境,它只为诗人而存在,没有对外的入场券。语言的侍卫守在门口,仅仅通过写作,他与世界和自我建立联系。将目光收回聚焦于内心,在与自我的对话和反驳中完成诗歌的写作,同时也完成对自我的确认。他只为自己而写,在写作中雕刻自己的头像。真正意义的写作上来说,诗人并不需要读者和这个世界,相反是读者和世界需要诗人。
胡桃是一座学校
(独白:学校是一只胡桃)
绿眼胡桃,饱满货郎的
一所白天,绳索下
眺望河床上的床单
(独白:从火车中擦掉
豆色的头,灰色的头)
胡桃拔尖的山坡上
它在口袋里装着墨水瓶
我们机械边找到洗手的药水
(《胡桃与独白》)
“没有神秘,也就没有诗歌。没有晦涩难懂,也就没有身体。”这一只角的野兽,为一种秘密的激情所挟裹,在体内的空虚与暗喜之水冲涌激越之下,将错位时空的几块碎片补缀成一块蓝印花布。这些收集、珍藏的彩色糖纸或马赛克瓷砖,在意念的拼装之下,成功复位,焕然一新。踩踏花丛之后,它的所见与表达必定是与众不同的。《螺蛳文本》是另一种拼贴,更大的拼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本,在一个总引子或者小序之下,是不同场景、不同想象的六章诗歌,那就像这个文本有六种不同的写法,有六种可能性,如同一个生命的多个侧面。也许这些侧面同时或先后在他的生命中存在过,但当它们被并置在一起,就显示了生活向多方面敞开、向多方向生长的面向。
面对他这一隐秘的书写,诗歌写作仿佛就不仅仅是“积德”,“它又像与人间交恶”。而他竟然认真给出了一个解释:“诗一方面用来交流,另一方面,它也希望隔绝。在交流中独立”,这里显出了车前子的一份厚道。而阿兰·巴迪欧则更直接:“诗不存在于交流之中。诗歌没有需要传递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表达,是一项仅仅从自身获取权威的声明。”而且从根本上说,诗人只有写的义务,没有解答的义务。一个诗人向别人解读自己的诗歌,就像向人坦白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是一种残酷的刑罚。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诗是无法解释的,但并非不可理解。”搭成恐龙的积木,一旦拆解,它会碎成一摊积木。但诗人并不打算告诉你这是一只恐龙。
与有的诗人将诗歌无限拔高不同,车前子一直努力在做着减法,为诗歌祛魅,剥去金边,还其真身。但是,如前所述,他说“诗接近尖端科学尖端科技”,在不自觉间又将自织的锦袍披在诗歌之上,或者说往诗歌上加载自己定义的头像。这是一种矛盾。它的原因在于诗人对一类诗歌极端的爱与对另一类诗歌极端的恨。你拿掉了一些东西,你必将放一些东西上去。矛盾,常常代表了更内在的真实。
3
如果要问车前子关于诗歌的看法,我相信他会这样回答:“诗歌在我看来,是一个奇谈怪论、想入非非、不得而知的——乐园。”好玩或乐趣,是他的诗歌的第三个关键词。写诗近四十年,他不仅没有一点停止的迹象,而且越写越放松,越写越贴近自我,从写作中体会到了特殊的乐趣。从新唐诗,到原样诗人,到行为主义……他在玩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在2007年前后,车前子和苏州的一批诗人、艺术家同人一起办过一个民刊名称就叫《玩》。而在《再玩一会儿》一诗中,诗人对自我(或诗人群体)进行了严厉的审视与回顾。一个人是一切人,一切人又是一个人。“是我。再玩一会儿吧。”这单独成节的诗行,我读来总感觉它是来自那最高的立法者,他也感到了寂寞,也冀望玩的快乐。但也许它是诗人对自己的召唤和规劝。这种玩的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精神和状态,没有利害考虑,没有崇高目标,它关注的是“玩”本身,在卸下一切之后,精神之眼准确地窥见艺术的纯粹与自由。我觉得,玩恰恰是他几十年保持诗歌写作旺盛生命力的秘密所在。道德真理、人间大义容易让人生累生厌,而玩乐却没有尽头。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先生在《别玩了,费曼先生!》一书中说到他在科学上取得这么大成绩的秘诀就在于玩,喜欢什么就玩什么,只考虑爱好与快乐,不管其他。在最高的准则上,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
在《即兴(独角兽之五)》一诗中,车前子对此进行了淋漓尽致的书写:
前卫风度的独角兽,
没有人文关怀。它是兽,
你让它证明什么?
它是独角兽,从黄色的宫殿,
突围,进入;
象牙塔,花梗一样烂掉。
它所有的奋斗,为了乐趣——
把自己想象为前卫风度,一种乐趣;
没有人文关怀,一种乐趣;
把自己想象为能够突破和一座——
黄色的宫殿,一种乐趣;
把自己想象为恶魔,乐趣更多。
花梗一样烂掉的象牙塔是另一种乐趣。
把自己想象为是独角兽的一只独角兽,
就像把自己想象为是人的一个人,
高高秋月挂长城,那一个人在这里。
这几乎是他的自我写照和宣言书!乐趣,乐趣,再说一遍他关心的只是乐趣,或者更多的乐趣!最后一句“高高秋月挂长城,那一个人在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那一个人在这里”,就是“我”,诗人自己,他为乐趣而生。在玩中品味、感受诗歌的乐趣,它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放松、打开,一种超脱了凡尘负累的轻逸状态,随时都能将诗歌收之在手。与此相联系,是诗歌写作上的“年轻态”:
“诗创作对我而言永远是开始,我愿做一个学徒,做到老。”在这样一个“乐园”里,永远不用担心开始得太晚,也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所写的,每天都乐此不疲地开始新的玩法,新的实验,尽情地享受着语言的狂欢,那些像水红菱一样新鲜的诗意也就在一个不自知的瞬间浮出了荷塘的水面。而在编织诗歌的织物时,他又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以一个“学徒”的心态,将诗歌写到语言的极致。
对于这种语言的狂欢,车前子并非没有反思,他写出的一系列极简之作,可以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平衡,或狂欢之后的平复。我甚至觉得,他在《即兴(猴子)》中提出了一种自我警醒的暗示:
我终于忍痛割爱。
放走那只与我常年为伴的猴子,
它毛色蜡黄,像纵欲过度的措辞,
”除此之外,一筹莫展。“
蹲在夸张的两腿上面,猴子
大概至死也不会明白我的苦心。
放走它,对我俩真是酷刑。
当语言如毛躁的“猴子”一般总是按捺不住地哗哗流淌,他开始意识到语言过度使用的问题,学会“忍痛割爱”。2015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正经》,但他并没有变得“正经”起来,不再玩了,而是他更加“一本正经”地玩,自得其乐地玩,因为玩,是一种文化本性。
4
车前子对汉字有一种迷恋。他不止一次谈到汉字的独特魅力,它与我们周遭之物的秘响旁通。稍稍回想一下汉字久远的历史,就会惊异于它几千年间的流传有序和对当下事物仍能保持准确指涉。一个黑方块的汉字,就是一块碳黑同位素,可以测试几千年前的沧桑风物,它的身上叠合着不同时期的历史身影。每一个汉字都暗藏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密码,它像一个在时间的流沙中不断被包裹、加密、压实的琥珀,那是致密之核,一旦打开就会爆出丰富的诗意。
“从汉字出发,抓住直觉,暂且把诗歌放在一边;抓住欲望,暂且把知识放在一边。”这是车前子关于如何写诗的经验之谈。字思维是他的第四个关键词。在他这里,汉字和直觉、和想象紧密相连,几乎是等同的。有诗友说到,与其他诗人依靠情感、回忆或现实触发写作冲动不同,面对一个汉字,车前子就可以产生一种自发写作的内在冲动。一根隐形的导线将他与汉字联结起来,他对于汉字有一种灵魂附体般的体悟,在相遇的那一刻如有神助般将汉字的蓄积信息挥发到极致。其最典型者,是利用汉字的歧义或谐音来制造诗意碰撞:
湖中的羊毛,水在涨
垫高牧羊人
夜潮下面
厚厚的一层
水在涨,涨过那里
才算看到
垫高的牧羊人
我想我已经长大
不需要主见
(《父亲》)
在诗人的笔下,“父亲”摇身一变化身为“牧羊人”,那也是上帝的别名,他还有另一个别名:主。我“不需要主见”,其实是不需要“主/上帝”之见,因为“我已经长大”。这最后两句中暗含的两种涵义,像拔河的两端,蓄满的张力让语言的绳子震颤不停。其他如“我们睡大 觉 觉得不错”的粘连(《流畅的时代病》)、从“干巴马”到“干爸爸”的滑动(《上校泥巴》)等皆类此。《柱十四根》一诗将则谐音特点发挥到极致,用读音为“zhu”的一组字,通过并置、组合的方式来结构诗歌。他还写过《柱一根》、《柱两根》……,也许这只是他所写的关于“柱”的系列诗歌之一,但你也可以认为它是用十四根“柱子”(这首诗里,读“zhu”音的刚好十四个字)撑起的屋顶。毫无疑问,这是游戏之作,是思维和语言的练习。除了谐音,车前子还充分利用汉字象形的特点,比如《编织车间》是一个“人”字的矩阵,横向16个、纵向7个。我第一眼就想起了纺织车间里一排又一排的纺织女工。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
不
止
上上
上上上
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左面增加一撇一竖:不,止!》)
这里是谐形,这可能是象形汉字更为根本的特点。“下”加一撇成为“不”,“上”加一竖在为“止”,上下对称,它是汉字的生长,同时也是文化的生长和历史的生长。而“不止”似乎又暗示着这种生长的没有尽头,生生不息。这些一字排开的方方正正的字符串,仿佛活字印刷里的一个个活字,又如秦始皇陵里面目安详而又始终沉默的兵马佣,在绵延、亘远的历史长河中,逼视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