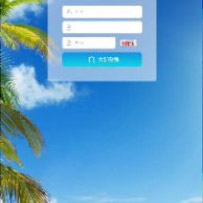双抢
再过五六天就立秋了。三十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大概还跟在父母后面紧张地插着晚稻田。由于我家田地多劳动力少,所以每年“双抢”总是临近立秋才能结束。
“晚稻不过秋,过秋九不收。必须在立秋前把所有的田都插完。”父亲常常对我们说。每每忆及这句话,我眼前多半会闪现那片像变魔术一般由黄转绿的田野。
要抢种,先抢收。当梅雨季节进入尾声,一年一度的“双抢”就开始了。风吹稻浪,遍野金黄——记忆中,那片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观,像极了梵高画笔下的田野。于我而言,却无美感可言,甚至掺杂着几分惧怕。在炎炎烈日之下,这黄色的田野闪出太阳一样刺目的光芒,站在沉甸甸的稻穗面前,我流汗的身体总是忍不住地打寒战。
记不清我是几岁开始参加“双抢”的,印象中的“双抢”更多地停留在未成年人时期。每当季节进入一年中最热的光景,知了的叫声疲软乏力,暑假就开始了,接踵而来的便是“双抢”。暑假约等于“忙假”,它和“双抢”近乎无缝对接。那时候,农村孩子的暑假与“休假”无关,与“血与火”的“烤验”有关。
对于漳湖的孩子来说,“双抢”尤其令人瑟瑟发抖,因为漳湖田园广阔,包产到户之后,人口较多的家庭,田地面积都在二十亩以上,而且这些田地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最远的田地离家有好几里地,远到没时间回家吃饭,只能就地埋锅造饭。为了多产粮,几乎所有家庭都将大部分田地用于种植双季稻。更可怕的是,漳湖田园地势极低容易积水,如果是在雨水刚结束后收割,泥土还是烂的,脚容易陷进去;如果是涝灾过后,则要在没膝的水中“捞割”稻穗子了。
提前收拾好晒谷场,给脱粒机上好油,再将镰刀一一磨亮,父亲在一个清晨领着面色发黄的孩子们,来到自家田地。他弯下腰,割下第一棵稻穗,拉开了我们家的“双抢”序幕。
“双抢”启幕之后,村庄变得安静起来,喧闹声转移到了田野。刷刷刷的割稻声与嗡嗡嗡的机器脱粒声从各家各户的稻田传出,交织在一起,合奏成田园交响曲。在我童年时期,水稻脱粒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用最原始的摔打戽桶方式,直到小学高年级时,脱粒机才开始出现。印象中,脱粒比割稻子要舒服一点,因为脱粒可以站着进行,而且有荫棚遮阳。不过,这项工作不适合孩子,因为脱粒、灌装稻包、拖移脱粒机都需要一定的气力。所以,年龄小的孩子干得最多的活是捡葡子送给大人脱粒;年龄稍大一些的则是割稻子(俗称放葡子)。
弯腰割稻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农活之一,因为劳动者不仅要忍受烈日的暴晒,而且稻叶频繁摩擦手腕,令皮肤火辣辣地疼,比腰酸背疼还要难受。至于被镰刀划伤手脚的经历,想必参加过“双抢”的人都有过。
我家有七口人,爷爷年纪大了,不参加田间劳动,主要负责摊晒稻谷之类的轻松活儿。母亲要操持洗衣做饭等各种家务,参加田间劳动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双抢”工作主要是父亲带领孩子们完成。
收割完一块田,再转移到另一块田,经过较为漫长的割稻、脱粒、运稻、锁草、移草等一系列工序之后,一望无际的黄色田野在父老乡亲勤劳的双手之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整整齐齐的稻茬,衬托着田野的空旷。
抢收任务结束,紧接着就是灌溉、翻耕,在收割完的田里进行年度第二次耕种。这一过程与插早稻田差不多(详见漳湖旧事∣插田),不同的主要是天气。插晚稻田正是三伏天,田里的水在烈日的炙烤下,很烫脚。多年以后,我在琢磨“汗珠摔八瓣”的意思时,就曾经联想到在那发烫的水田插秧的情景——上晒下蒸,导致人的汗水不断滚落水田,激起水花瓣瓣。
所以,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插田和收割一样,都要起早趁凉。天刚蒙蒙亮,就赶到秧田去拔秧,为白天插秧做好准备。
印象最深的一次“双抢”,是父亲带着我和妹妹完成的。那一年夏天,勤劳能干的二哥不知何故,不辞而别去了外地,仿佛是离家出走,迟迟未归;暑假来临时,刚做代课教师不久的大哥和几个朋友相约“闯荡江湖”去了。父亲母亲的愤怒和焦虑可想而知,但苦于无从寻找,也只能徒叹奈何。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初中生,暑假时,我天天盼着大哥二哥回家,想念他们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双抢”将至,一想到如此巨大的抢收抢种工程没有大哥二哥的参加,我头皮就发麻。但是最终,大哥二哥在外地舒舒服服地躲过了这年的“双抢”,我和妹妹则成了劳动骨干,累得差点吐血,一直“挣扎”到临近立秋。
扛稻包、拉板车、将粪肥运到三里地之外、天气突变时抢收晒谷场上的稻子……这些我亲身干过的重活累活,即便是过了三十余年,依然让我感到疲惫。如果要说“双抢”记忆中最大的享受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收工后跳到河里洗个澡,洗去一身的汗臭和疲乏。
艰苦奋战一个月,“双抢”总算结束。每每站在前河堤上,望着那一转眼就换了绿装的田野,内心免不了要钦佩父老乡亲的伟大,但更大的感受却是,做农民实在太苦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努力走出这片田野……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我的父老乡亲,如今双季稻已退出家乡的历史,你们守望的田园早已失去昔日的喧哗。沟渠中的水越流越细,条条阡陌越来越瘦,狗尾草与蒲公英却是一年比一年茂盛。板车辙与牛蹄印里长出了细密的杂草,在夏风中婆娑、幽咽,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年我们抢收抢种的往事。
罩子灯
又是一年清明节。傍晚,我独坐书房,追思遥祭。今年是父亲去世的二十周年,二十年虽然很久远,但是父亲的面容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在时光遂道的深处,总有一些明亮的东西伴随着他,比如刀锋、玻璃杯、罩子灯,这些东西曾经照亮我的前行之路,后来就一直照耀着记忆中的父亲。
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如果此刻我需要一盏灯,我希望是一盏罩子灯;如果此刻我要回忆,我想回忆一下父亲的罩子灯。
父亲是一名农民兼木匠,与各种刀具和铁器打了一辈子交道。别看他干的是粗活与脏活,对待家庭生活却颇为讲究,比如,他每天早上会把家里的茶杯洗得锃明瓦亮,傍晚收工时会把农具或木工工具擦拭得一尘不染。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家里的罩子灯在他的悉心呵护下,总是散发出夺目的白光。
罩子灯是油灯的升级版,在没有通电的年月里,油灯是乡村唯一的照明工具。小时候,我见过的油灯有菜油灯、柴油灯和煤油灯。菜油灯是最原始的灯具——在一个小碟子里盛放少量菜油,再在油里放一条灯芯草,便可点燃用于照明。其缺点是亮度太小,所谓“一灯如豆”便是对此灯光的生动写照。与菜油灯相比,柴油灯在亮度上大有进步,但是烟太大,没有推广价值。而煤油灯在燃烧时所产生的烟较小,可以用玻璃罩罩住火苗,使之产生聚光作用和防风作用,并且玻璃罩不容易被熏黑,因此亮度更高,应用更广泛。这样的煤油灯也叫罩子灯。
那时候我总觉得,父亲对待罩子灯比对待儿女们还要细心。天一擦黑,无论收工后多么累,父亲照例会将罩子灯拿到门口,借着天光清洁一番。先是将大肚子玻璃灯座擦一遍,再用旋钮扭出灯芯,拿剪刀将燃烧过后的黑色灯花剪掉,接下来就是擦拭灯罩。这是最重要且耗时最长的步骤。父亲用嘴对着灯罩的圆口,朝里面哈一口气,接着就将干净的抹布伸进去,小心翼翼地转动。玻璃罩在抹布的摩擦下,发出“布谷布谷”的声音,十分好听。擦完之后,他还要眯着眼仔细检查一番,确认玻璃罩纤尘不染、透明度达到极致,才肯罢手。
擦灯罩这活儿,孩子们其实也可以干,但是父亲对我们的“笨手笨脚”不放心,特别是有一次我因用力过猛将灯罩擦破裂了之后。灯罩破裂容易伤手,父亲因此也不敢冒险给我们练手。擦灯罩确实是技术活儿,那玻璃很薄,罩口又小,擦拭的时候要掌握好力度,还要有很好的耐心。父亲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所以擦灯罩总是亲力亲为,并且不厌其烦。起初是每天擦一盏灯的灯罩——因为经济条件差,只有堂屋的灯盏配有玻璃罩。后来随着四个孩子陆续入学、升学,无罩的煤油灯难以满足夜晚写作业的需求,父亲先后添置了两个灯罩。这样一来,擦灯罩就成了一件不小的任务。
由于父亲擦得勤,我家的灯罩很少出现被熏黑的情形,只有当父亲离家多日,罩子灯才会暗淡下来。比如,去江南驮树,或者去外乡挑坝,父亲必须在当地住宿,家里的罩子灯就失去了呵护。母亲对灯光的亮度没那么讲究,并且也因为忙,所以不怎么打理灯罩。父亲一回来,罩子灯就有了鲜明变化。划亮一根火柴,点燃灯芯,罩上玻璃罩,微弱的灯火顿时大放光明,令四壁生辉。
记忆中的夜晚,我家的屋子总是比别人家明亮,从村外走夜路回家,我们的脚步习惯于朝那最亮的光点前行。
罩子灯的光明温暖了全家人的生活,照耀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如今想来,父亲对罩子灯的悉心呵护,何尝不是对家人的一种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