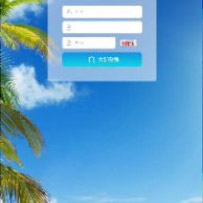张建新的诗歌对我来说充满着诱惑。
记得很久以前读到过他的一首散文诗《烂掉的寻人启事》:
宽大梧桐树叶覆盖着一条道路的梦。
肯定有很长一段时间清洁工不曾来这里打扫了。地上满是落叶、废弃的垃圾袋和纸张。街道依然与往常一样承受着欢笑与嚎叫,承受着狭窄天空洒下的雨水、阳光。
两侧墙上和电线杆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聘服务小姐、招聘机修工、保安与会计。没人关心你从一个地方消失或者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一则寻人启事像一个痛苦的怀旧者,在众多广告的夹击下显得多余而苍白。它上面的照片已在一阵紧过一阵的秋风里烂掉了,只剩下模糊而抽象的象征,如年龄、身高。
一则寻人启事的无用之处在于:在不断的企盼中,它要寻找的那个人已经面目全非。
由一则寻人启事,作者联想到商业文明的背景下,一个人自我的迷失:“在不断的企盼中,它要寻找的那个人已经面目全非。”这在我的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作者由司空见惯的小事物,表达的人的生存的大主题,观察不可谓不独到,构思不可谓不巧妙,主题不可谓不深刻!
但是,正是由于建新的人生体验独到和深刻,表达巧妙,所以他的许多作品对于读者的理解来说或许充满一些挑战。我由于工作一向繁忙,加之对诗歌也是停留在业余爱好的水平,所以对建新的诗歌虽然充满兴趣,这里也只能做些尝试性的浅探。
我以为,诗歌是心灵的历史。既然要抒写抽象的心灵,那么就要去寻找表达心灵的东西。那怎样才能让心灵现身?“圣人立象以尽意”,古人的方法就是找意象---表意之象。传统诗歌表现手法中的赋比兴中的“比”就是“立象”的源头吧,“赋”与“兴”起着必不可少的交代和起承转合等作用。
观察建新诗中之“比”与诗中之意象,感觉到他在“尽意”中尽显灵性之挥洒与想象之飞扬,让人尽收意外之喜悦,为他比喻之奇与信手拈来之巧拍案叫绝。且看《清晨雨濛濛》
收回晾在阳台上的衣服是雨
命令我做的事,出门时
我和它的关系演变成雨衣和它的关系
雨不大,更像是濛濛雨雾
毕竟,它已经存在了一个晚上
我需要认真对待
斑鸠在树丛里潜伏,我发动
摩托车的声音惊飞了它
它逃脱了我下坡时的失重感
路边的草叶更黄了,衰微的湖水
一眼看尽,进入这样的景致
非我所愿,疾奔的人生时刻
需要一个目的地,卡车经过时
飞溅的泥浆落到我身上
它也有一个被雨水带飞的人生
想来,这也许并不残酷
意外的事比比皆是,早晨和夜晚
没什么不同,当你不愿看到
这一切,就会有一堵无形的墙
竖了起来,如这濛濛雨雾里
未知的前方,这曾停留过暮色的清晨
(刊发《上海文学》2022年5期)
诗中一只被惊飞的斑鸠被说成“逃脱了我下坡时的失重感”,飞溅落到我身上的泥浆居然“也有一个被雨水带飞的人生”,从“我的失重感”“也有”这些用词眼,我们能品味出作者要抒发的人生感受,只不过避免了直接抒写,而通过即事即景自然带出,效果更佳。这就是建新之“巧”!再看《可能有另一种生活》:
似乎总是在厘清自己
以此来表明自己在日常分野里
仍然保持的正常性
但越来越艰难,越来越
不愿说出那独一无二的不
以规避不解的责难
哦,这当然不能怪你们
我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像我梦到的指纹
还没找到应该属于哪一枚按钮
我甚至不期望能找到它
鸟儿从树枝上飞下来
光线里缠绕着某种看不见的神秘
我们可能更多是
在这种类似的神秘中活下去
(刊于《星星诗刊》2022年4期)
诗借“鸟儿从树枝上飞下来\光线里缠绕着某种看不见的神秘”,来表现诗歌创作的精神状态,那是一种摈弃世俗功利带自带神圣光芒的神秘状态。《文心雕龙·神思》有对这种神秘状态的描述: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经常沉浸在这种状态下,自然不会被功利社会所理解,又怎么能轻易“厘清自己/以此来表明自己在日常分野里/仍然保持的正常性”?
我要说的是,这种非常抽象的心灵感受,作者通过一幅日常画面把它表现出来,可见他捕捉意象并加工到恰到好处的能力非同寻常。
类似这样的比喻或意象,在建新诗歌中俯拾即是,比如《秋日登高》(刊于《星星诗刊》2022年4期)、《写作的宿命》(刊发《上海文学》2022年5期)、《春日迟迟》(《诗刊》2017年7月号下半月刊“双子星座”栏目)等。
在一首诗歌里,众多意象可以构成一种意境。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诗中所写之场景、生活画面、自然景物之类与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的相互交融,让人沉浸其中,受到感染的一种境界。
从意境的角度,我感觉建新的诗歌意境深邃,境中寓理。且看《语言的被动性》:
雨中,两只麻雀仍然立于
电线上,如果只有一只
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孤独或落寞
雨雾里事物有淡淡的模糊性
随手摘下一枝,像极了你想要的语言,
但又不是
喝了口茶,再向窗外望去
麻雀已经不在了,只有
滴着雨水的电线,
雨雾更浓
它在向你内心的需求扩散
内心是语言的丛林,在那里
寻找到一只还是两只
麻雀,它还没有想好
(原载于《安徽作家》2023年第3期)
这首诗不是简单用“比”,这里有中心意象“麻雀”之外的物象或者说意象“雨雾”,还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着的景象,这就构成了意境。借这个意境,建新表达“语言的被动性”的主题。这让我想起钱钟书《咬文嚼字》,他说“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感情,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我们可以将这段话与《语言的被动性》的最后一节对照着读:
“雨雾更浓
它在向你内心的需求扩散
内心是语言的丛林,在那里
寻找到一只还是两只
麻雀,它还没有想好”
我以为第一个“它”是指“雨雾”,第二个“它”是指内心。第一个“它”导致第二个“它”还没有想好,也就是还在做“思想感情上推敲”。所以,我以为,这首诗体现了建新在诗歌创作中深刻的领悟与思想性,同时,这些领悟与思想,在诗中并不流于说教,而是通过意境形象呈现出来的。《给自己写首诗》中的“林中小屋”、《冬日晨雾》中“冬日晨雾”,都是作者营造的意境,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我同时注意到了这两首诗似乎都有些卒章显志的味道,最后轻轻一点就让诗歌前面的描写一下子变得意味深长,有了意蕴。
《给自己写首诗》的结尾:
“是的,我不会这么做,我不能
亲手毁掉事物之间那脆弱的独立”
“脆弱的独立”是脆弱的,更是宝贵的,也是作者小心呵护的。
《冬日晨雾》的结尾:
“在可怕的“一直在”里,
我们活了这么久”
这个结尾一下子让“冬日晨雾”获得了象征意义。
以上,从比兴手法到意象选择再到意境营造的角度简单赏析了建新的一些诗作,可谓管中窥豹。建新诗歌创作颇丰,成绩斐然。虽然说“诗无达诂”,从读者的角度,读者可以有读者的解读,但鉴于本人水平有限,以上就算是对建新诗歌艺术的一种浅探吧。
附录相关诗歌:
给自己写首诗
给自己写首诗,是给
不说话的林中小屋打通一条小路,
我这么一直看着它,直到
它成为我的一部分,于是我
似乎也有了浓荫的清凉,
但我知道它仍然不会说一句话,
屋顶枯叶被暴雨冲了下来,
泡桐树的紫色花落在黑瓦上,
鸟儿们从清晨就开始鸣叫,
与冬天在雪地里的叫声不大一样,
并没有一条专门通往小屋的路,
我也不记得从哪条路上离开它,
覆于其身的光泽变得诡异难辨,
但只要我愿意,在杂草和碎雪中
它可以为我打开任何一条小路,
而且每次都不会重复,
是的,我不会这么做,我不能
亲手毁掉事物之间那脆弱的独立
(来源:《诗刊》2017年7月号下半月刊“双子星座”栏目)
冬日晨雾
我们通常说:雾散了。
可雾都去哪儿了,我们不去追究
早晨七点左右,雾突然升起来
才被我们看见,也看见自己如深渊羊群
西外环,车辆行得缓慢,我感到
头发与睫毛慢慢变得湿漉漉的,
但终可在经验里到达医院
我掏出手机,拍下朝雾后面的云层
和隐约的太阳,拍下身边的树
池塘和朝向雾中延伸的花格子方砖小路
雾来去无由,我期待的意外并不会出现,
在可怕的“一直在”里,我们活了这么久
(来源:《诗刊》2017年7月号下半月刊“双子星座”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