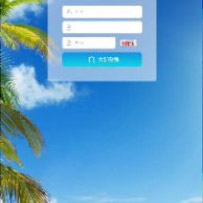绿豆与大米的结合,不知道会在大家脑海里产生哪几种画面?
我酷爱豆类,唯有绿豆我不爱吃。不过一种由绿豆制作的食物却是例外—— 豆丝。它属于我家乡的特色美食之一,制作原料就只有绿豆和大米,制作的过程称为“拓豆丝”。“拓(tà)” 是我从乡音偕音而来,取其字义中的“推开、张开”之意对应豆丝的制作手法。
我生长在皖西南,拓豆丝是家乡一件很隆重的事。每年秋收过后,家家户户都会认真准备。一来庆贺一年来的辛苦劳作所得,二来为数九寒天准备干粮。拓好的豆丝煮起来方便,不费时,不费力,最主要的是好吃。
新鲜的大米,洗净之后用常温水浸泡上24小时,大米选材很重要,米质太过粗糙,口感不好;米质太糯,制作时容易粘锅。绿豆用石磨将壳与馕肉分离,同样用常温的水浸泡上一个昼夜,为了绿豆的口感和颜值,主妇们都还要特地用篾筛将绿豆壳捞出,最后将洗净的大米和淘过壳的绿豆掺在一起,掺的比例通常是“对半掺”,也就是各百分之五十,再用石磨将它们磨成浆。按照惯例,都是头天早上浸泡好这些原材料,第二天早上一家人就开始进行后面的工序,年轻、有力气的人推磨;年纪大一点的,就用勺子有节奏地、均匀地一勺一勺地往磨眼里添加这些浸泡好的食材,也称添磨。一般都是清早起来开始推磨,到日头西下时才能磨好。
掌灯时分就可开始进行最后一道工序了——“拓”豆丝正式开始。
锅洗净,柴备好,锅要用磨锅石磨得光滑铮亮,不然制作的豆丝粑(即未切、整块的豆丝)容易破。柴火也有讲究的,一般都是事先备好的、从松树林里耙回来的松针,不仅是因为松针易燃也易灭的特性适合拓豆丝,更因为松针燃烧散发的松香融进米香与豆香中,赋予了朴实的食材更富层次的口感。等大铁锅烧热,再抹点油,用葫芦瓢舀出适量的米浆倒入锅里,倒浆时用瓢沿着锅的中部淋一圈,然后用河蚌壳把浆在铁锅内壁均匀地摊开来,让它形成一个实心的圆,盖上锅盖,食材与期待一同升温。同时,在另一口铁锅里进行同样的操作,完成后再回过头来对先前的锅进行迅速的掀盖、合盖动作,反复两次,等到第三次掀开锅盖时,已经熟了的豆丝粑边缘就会自动翘起,只要用双手轻轻一拎,一个散发着迷人香气、带着二分之一铁锅轮廓的圆圆的豆丝粑就出锅了。
一个豆丝粑的制作用时约两分多钟,就这样,大人们挑灯夜战,豆丝粑一个接一个地出锅,往外出的不仅有豆丝粑,还有站在灶台边等吃的我们那不争气的口水……
但是,小鬼的馋并不能打动讲规矩的母亲,我和弟弟是吃不上第一个出锅的豆丝粑的,前三个要用干净的碗装好摆在灶台上敬祖宗,第四个,妈妈则会放到我手上,嘱咐我送给爷爷吃。我总会像拿到接力棒似的一口气飞奔到爷爷面前递给他,再光速回到灶台,用灼热的目光加热那个属于我的豆丝粑,等到在灶膛前烧火的长辈们都尝过后,终于轮到我和弟弟,大人们一句“当心烫”还没说完,我俩已是以表情包似的模样大口吃下,那一瞬间,仿佛升入云端……
大块朵颐之后,回神凡间,一切要按照妈妈的吩咐来。将刚出锅的豆丝粑送到大伯、小奶,三婶、四姨家,"快送去,让他们趁热尝鲜",妈妈边说,手上拓豆丝还在继续着,每每从邻居家送粑回来,妈妈又会递上新鲜的豆丝粑,让我赶往下一家。
豆丝有多种吃法,刚出锅的豆丝粑卷成圆筒状,放凉,再切成丝状,留一小部分可以就这样原汁原味新鲜吃上好几天。把切好的豆丝与猪肉或牛肉一起炒,也是我们家乡用来招待贵客的一道特色菜。不过为了能留住美味,制作好的大部分新鲜豆丝,我们次日会在太阳底下晒干。因此为赶上好天气,在拓豆丝之前是要特意关注天气预报的,天气不好是不能制作的,不能晾干就会糟蹋粮食。晾干后的豆丝,能保存到很久,即使来年春暖花开,白菜长菜苔的时候,抓两把豆丝加菜苔一起煮,鲜美不减,还增加了干货独有的香气,那种美味无法用文字描述!
晒干的豆丝还是送礼佳品,张家姑娘来了,李家侄子来了,都会送点给他们带回去。豆丝也不仅仅是豆丝,它还是乡邻们增进感情,化解矛盾的好媒介。张家和李家在种田时闹了点小矛盾,送点豆丝,握手言欢;王家有女,李家有儿,想做儿女亲家,豆丝就串起了姻缘……
时代发展到如今,食物的多样化,让我们的餐桌丰富起来,但我们家乡的拓豆丝风俗至今还一直沿袭着,更增添了些许年味在里面,为了让长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能尝到现作的豆丝,家人们总是等到他们腊月返乡时再拓豆丝,拓了豆丝就过年。另一个变化就是现在的电动机械代替了以前的人工推磨,大大降低劳动强度。过完年外出打拼的儿女们,后备箱里塞得满满的,这里就少不了豆丝。回到大城市里,加班后的疲倦、受委屈时的无奈、长时间的孤独,我们总不会忘记煮一碗豆丝,从锅中飘出的热气与熟悉的香味,是家人借由它给予的拥抱与安慰,总能让我们一次次整理好情绪,被疗愈后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