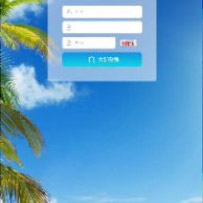麻塘冲,坐落在南北两座山包之间。一条水泥路横贯其间。站在水泥路上向东眺望,是春草绿茵茵的泊湖之滨。向西眺望,一条大坝横亘在水田的尽头,坝里拦隔的是一方清清水塘,名曰“麻嘎塘”。老人们说,“麻嘎塘”从未干涸过,就是历史上最干旱的民国二十三年也未见底。塘下受之灌溉的千亩良田,当地人称之为“麻塘冲”,其得名大概缘于此塘吧。
两座山包之间原本不规则的水田,被两旁纵向排洪沟切割得整齐划一。横向的一条条田坝又把整个大长方形的田块分割成无数的小长方形,每块小长方形田块面积均在七亩上下。中间一条小型灌溉水沟又把水田一分为二。灌溉、排洪都很方便,麻塘冲堪称当地老百姓的“粮仓”。
这样错落有致的田块是谁的杰作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麻塘冲掀起了一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浪潮,他们仅用一双手和一副肩膀,一把锹,一担土筐,一根扁担,把原来大雨大灾,无雨旱灾的各种形状的小田块,修建成了防洪排涝,引水灌溉,便于机耕的大型田块。虽没有大寨梯田的风格,却有千里平畴的广袤。站在麻嘎塘坝上向下眺望,一望无际。
尽管刚开始的几年,由于田地整体性进行了翻挖和搬运,过去肥沃的土壤几乎荡然无存。粮食产量并没有增产。然而,给今天的机械化操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抚今追昔,我常常在记忆里极力搜寻昔日的麻塘冲。那里曾经是阡陌纵横,沧海桑田。汤屋,舒屋,老林头,郑家代屋,方家陈屋四个屋场的田地穿插期间。四斗丘,鞋底丘,神树田,三角丘,葫芦田……这些具有方言色彩的田名早已写在我记忆的深处。
不仅如此,甚至梦中无数次来到童年摸蟹子和捉泥鳅的堰沟旁。
麻塘冲在没有平整前中间有一道堰沟。从麻嘎塘起,蜿蜒而下,流向泊湖。晴天堰沟里流水淙淙,一旦下雨天,周围山包上流下的洪水冲入堰沟,流水漫过堰坝。从南到北,周围的村民到田间劳作,靠踩着几块石墩过堰沟。我们小孩踩在石墩上,腿脚发颤,连石墩都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年轻时的母亲,身板硬朗,挑起两箩筐稻子,走在石墩上,稳稳当当,脚踏石墩,节奏协调,稳如轻燕。
那时候读书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一到农忙,学校就放“忙假”,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的农活。看看牛,背背稻草,农家还是求之不得的。搞集体的时候,有专门耕田的农人,这是技术活,他们中午回家吃饭要专门安排别人看牛,那些看牛活自然而然落到小孩身上。
麻塘冲是我们几代人流血流汗的地方。
“五·一”假期,带着久违的期盼,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来到麻塘冲。我一眼就认出了当年我家的水田——“石榴树”。田边那棵老石榴树在初夏的阳光里沙沙作响。尽管树下的田是我家的,但岸上的树是舒姓人家所有。我们连牛都不敢拴在他家树上。那家女主人骂人很凶,谁都招惹不起。然而,树是很善良的,我们劳累之余,在树下乘乘凉,打打瞌睡,树是非常慷慨的。我们一家很感念这棵树。石榴树的位置在山包的旁边,位置很偏,因而不在土地平整的范围之内,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风从石榴树的田头飘然而过。当年父亲教我学耕田时蹲的田坝也还依稀犹存。
想当年父亲年老体弱,不能下田耕种,我接过父亲用牛的鞭子。父亲蹲在田坝上教我怎么开墒,怎么犁地,都是手把手地教。刚出校门的我,就是觉得“看花容易绣花难”,由于握“犁把”的轻重难以控制,导致铁犁耕入的深浅不一。牛累得直喘粗气,我自己的两只胳膊几乎也酸疼得抬不上头顶。
今天故地重游,旁边静静站立的石榴树显得更加苍老了。它用诧异的眼神瞅了瞅我,似曾相识一般。父亲和老水牛都已作古,那个田坝上留下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哪个是我的,哪个是父亲的呢?
大女儿出生那年,家里添了人口,本该进土地,可是生产队一直拖延,母亲是个性急耿直的人,亲自上门找队长理论。闹得两家口角不和。通过母亲的奋力争取,终于在沿河边分得了孩子的口粮田。可老天偏偏不作美,那年大涨水,快成熟的稻子一夜暴雨,全部被河水收割了。母亲暗自不知流了多少泪。
我们弟兄仨刚分家那年,我们商议,父母年事已高,不让他们种土地,把他的“责任田”我们“三一三十一”分摊了。我们三兄弟每人每年给二老五百斤口粮。一生勤劳惯了的父母,跑到“团鱼凸”的山旁开垦出一块荒地来,居然还种上了棉花,打算换些零用钱补贴家用。父母去世后,三弟接管了父母的荒地,土地贫瘠,广种薄收了两年,栽了两行松树,也算是对得起当年父母的良苦用心吧!
从麻塘冲回家之后我不禁想:在我家乡,过去每人每年上缴的农业税、乡管费等杂项费税高达四百元之多,乡民们都寸土必争,视土地如生命。如今国家减免了所有的税收,还有补贴,为什么对土地却不屑一顾任其茅草肆虐蔓延呢?
麻塘冲之行,回家后心里莫名地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