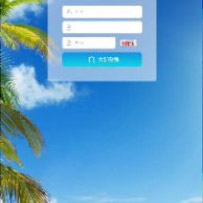那年夏天真是出奇的热,热到许多老人必须坐在大水缸里才感到性命安全,热到我的父亲母亲舍得拿钱来给孩子们买冰棒吃,热到我父亲愿意冒险投资让我大哥去做生意——卖冰棒。
小时候,我的父老乡亲们的降温措施很简单,无非就是吃西瓜、皮蛋,喝西瓜粥、绿豆粥。冰棒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在漳湖出现的,但由于价格不菲——香蕉味的五分钱,牛奶味的八分钱,雪糕要一毛五——因此多数人舍不得买。西瓜、绿豆都是自家种的,不要钱,成了降温的首选食材。不过,孩子们却不太喜欢吃这些不要钱的东西,而对冰棒情有独钟。奈何财政大权在大人手中,想吃冰棒只能碰机会,比如参加“双抢”劳动、跟大人去粮站卖稻,一般都有可能获得冰棒的奖赏。
对穷人家庭来说,吃冰棒算得上比较奢侈的事情,毕竟那个时候各个家庭的人口都比较多,吃一次冰棒付出的代价相当于几斤大米。我家有七口人,全家集体吃冰棒的事情在我记忆中仅有一次。在此之前,我常常觉得,我的父亲母亲大概不会吃冰棒,或者对冰棒毫无兴趣。他们经常说,冰棒只是表面降温,实际根本不“打凉”。
对于孩子们来说,吃冰棒主要不是为了降温,而是解馋。为了吃到冰棒,他们总是有办法的,比如,偷家里的钱,或者偷鸡蛋卖钱,或者谎称买橡皮本子或笔,向父母要钱。口袋里有了钱,就成天盼着“香蕉冰棒”的叫卖声出现。
学校,是卖冰棒的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消费群体集中并且不心疼钱,所以购买力较强。而且孩子们大多有攀比心理,看到别人吃冰棒,自己不吃,面子多少有点过不去。所以,学校下课铃声刚过,叫卖冰棒的声音就会响起。身上有钱的孩子便向声音奔过去。买了冰棒,多少想炫耀一番,因此都会拿到人多的地方吃。有时候,吃完了仍然会不停地咂着嘴,以向没看见自己吃冰棒的同学表明自己刚刚吃了。冰棒吃掉了,竹签还舍不得扔掉,收集起来,可以做“挑竹签”游戏。
那时候的冰棒,口味单一,初期以黄色香蕉味为主。所以,卖冰棒的人,总是骑着自行车打着铃铛,一路叫喊“香蕉冰棒”,叫卖的口音并不是望江本地腔调,而是安庆城里人的腔调——“xián- jīo -bīng -bàn-”。即便是后来增加了豆渣冰棒、牛奶冰棒以及雪糕等新品种,他们的叫卖声仍然是“香蕉冰棒”。有的人会变化一下,吆喝“香蕉豆渣冰棒”或“香蕉牛奶冰棒”。这样听来,“香蕉”一词似乎有了“卖”的意思。
自从我大哥也成为一名卖冰棒的人,我再也不羡慕那些经常在我面前吃冰棒的同学了。
那年夏天,酷热难当,父亲见本生产队小伙子立杳的冰棒生意做得不错,便决定把用于晚稻追肥的钱拿来作本钱,让我大哥也去卖冰棒。父亲通过熟人从日星供销社弄来一个用于装农药的木箱,将它洗干净,暴晒一天。然后自己动手,用棉绒和胶纸将木箱封得严严实实,再往里头放入一小块新做的厚棉被,用于冰棒保温。最后将做好的箱子在自行车后座上固定好,卖冰棒的设备就大功告成了。十六岁的大哥骑上自行车,揣着拨货的钱,跟立杳哥去了赛口冷饮厂,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经商。
家人卖冰棒,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大量冰棒可吃,毕竟,冰棒是有成本的,而且卖冰棒都是东奔西跑,与家人难得碰面。只有一天下来,冰棒没有卖完,我们才有得吃。但是大哥拨货都算得比较精准,很少有剩余的冰棒带回家。不过,到学校卖冰棒时,大哥通常都会挑一支有些软化的冰棒给我吃。
人算不如天算,尽管大哥拨货越来越有经验,但是如果遇到下雨,也难免会赔本。记得我去中洲中学参加小升初考试那天,早上还是晴空万里,等到考完第一场试,天就下起了大雨。考生们都站在走廊里看雨,这时候,雨幕中有人推着自行车往我们这边跑,到了走廊一看,原来是我大哥。他把自行车停好之后,向同学们兜售冰棒,说一支只卖三分钱。三分钱,是进货价,大哥想努力保本。但买冰棒的同学却很少。考试的铃声响起后,同学们陆续走进了考场,留下大哥一个人站在走廊里发呆。好不容易等到考试结束,木箱里的冰棒也开始变软了,大哥将冰棒售价降到了两分钱……
下午回家后,天是阴沉沉的,气温是清凉的。大哥到家比我晚一些,我注意到,他的自行车和木箱沾满了泥巴。父亲问是不是摔倒了,大哥点了点头。
那天傍晚,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吃起了冰棒,吃已经开始融化的冰棒。父亲和母亲也吃了几支,那时候我才知道,父亲母亲其实是很吃会冰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