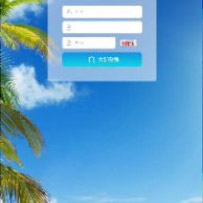不知不觉间,怀乡的文字已经累积了50余篇。也许还会持续下去。一待怀念的石子投入,便会荡漾起满池波光。
想到这,我不由得为脚下正踏着的土地叫屈。
合肥,一个我工作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地方。这座城市给了我体面的工作、温馨的家庭、熟悉的街巷。可当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脱口而出的永远是那个只在生命前十八年停留过的地方——安庆望江。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特有的"出厂设置":家乡这个地址,一旦刻进DNA,就再也无法被后来的任何城市覆盖写入。
我们这代人,像是行走的活化石,身上带着农耕文明最后的印记。祖先们在黄土地上"安土重迁"的文化密码,至今还在我们的血脉中跳动。就像我,能在合肥的写字楼里熟练使用各种办公软件,却总在不经意间,想起望江门口塘的涟漪,想起老屋梁上燕子筑巢的春讯。
中国人的家乡,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它是母亲灶台上蒸腾的雾气,是父亲田埂上深深的脚印,是童年追逐嬉戏的晒谷场,是祠堂里香火缭绕的祖先牌位。这些记忆的碎片,构成了我们认知世界的底层代码。
古人说得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望江的江水不仅养育了我的身体,更塑造了我的灵魂。那里的温润气候给了我韧性,绵延丘陵教会我沉稳,奔腾长江赋予我向往。这些烙印,是后来任何城市生活都无法格式化的生命底色。
在这个人人都在谈论"逃离北上广"的时代,我们突然发现,无论逃到哪里,都逃不出心中那个叫"家乡"的地方。它可能贫穷,可能落后,却始终像母亲的怀抱,永远为我们敞开。这让我想起唐代"网红"诗人贺知章的爆款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原来,一千年前的古人,早就参透了这份刻在基因里的乡愁。
现代社会的我们,像极了候鸟,在各个城市间迁徙。我们学会了都市的生存法则,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他乡闯出了一片天地。可每当深夜加班结束,走在陌生的街头;每当遇到挫折,需要一处避风的港湾,内心深处最先浮现的,永远是家乡的模样——可能是村口那棵老树,可能是儿时摸鱼的小河,也可能是母亲站在门口张望的身影。
这些记忆,就像手机里的云备份,随时可以调取,温暖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夜晚。
如今,在合肥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我,依然会在听到黄梅戏时驻足,在闻到蒿子粑香气时恍惚,在看到长江图片时悸动。这根"永远甩不掉的尾巴",这个"永远抹不掉的胎记",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反而成了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所以,当有人再问我"你是哪里人",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安庆望江。"这不是固执,不是怀旧,而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对自己生命源头的坚守。
也许,正是这千千万万个无法被覆盖的家乡地址,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地图。它让我们在漂泊中有所依归,在变化中有所坚守,在迷茫时能找到来时的路。
你的家乡地址,还刻在你的DNA里吗?在这个人人都可以随处流浪的时代,这份看似"过时"的牵挂,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定海神针。
观画·雪地里的一抹红
这幅画,静静地悬在墙上,却仿佛将一整个北方的、静谧而丰盈的年关,都收纳其中。
画中的房屋,是极尽简陋而质朴的。条石垒的围墙,透着山野的倔强;土砖砌成的墙面,风雨经年,已露出大块斑驳的痕迹,像一位老人脸上深浅不一的沟壑,诉说着岁月的磋磨。只是,一场酣畅的大雪,将这一切都轻轻覆盖、温柔地抚平了。厚厚的积雪压住了低矮的房顶,边缘圆润而柔和,像是给这座饱经风霜的房子,戴上了一顶圣洁而温暖的帽子。万物寂然,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一种颜色,一种声音——那便是雪的白,与静默的回响。
然而,若仅有这片素白,画面便不免于清寒与孤寂。最能动人心魄的,是那画家匠心独运、悄然点缀其间的几抹红色。
你瞧,那高高树梢上悬着的,不正是一盏红灯笼么?那红,不是怯生生的,而是饱满的、沉着的,在白雪的映衬下,像一颗跳动在凛冽空气中的、温暖的心脏。目光下移,门楣上那崭新的春联,是更浓郁、更庄正的红,那墨写的祝福,是这户人家写给来年最郑重的期许。还有那窗棂上,依稀可见随风起舞的窗花,那灵巧的红色图案,是民间手艺里剪不断的、对生活的热望。
但这所有的红,似乎都只是为了烘托画中那个灵魂——那位雪地里穿着红袄的媳妇。她仿佛是这白色世界里走出的一株红梅,鲜活,明媚。她左手提着一篮金灿灿的桔子,那明亮的黄与身上的红、脚下的白交织在一起,是那么的富足而和谐;她的右手,紧紧地牵着一个同样裹得严严实实的娃娃。我们看不见她埋在被风帽遮去的脸庞,却能从她稳健的步伐、从那微微前倾的姿态里,读出一种沉稳的、踏实的喜悦。她正从画外走来,要回到那个被雪覆盖的、亮着温暖灯光的家里去。
这一抹行走的红,瞬间便让整幅画活了过来。她不是被观赏的景致,她是这景致中的生命与呼吸。那红,是灶膛里不熄的火,是血脉里流淌的情,是寒天冻地中,一个家庭最坚实的温度与最蓬勃的生机。因了她的存在,那高挂的灯笼才有了节庆的欢愉,那门上的春联才有了情感的落点。
我久久地凝视着。画依旧是静的,我却分明听见了脚踩新雪的“咯吱”声,听见了院内隐约传来的犬吠,听见了那红袄媳妇推开家门时,满屋热气腾腾的喧闹。
原来,再朴素的岁月,只要有这“一抹红”在,便有了根,有了魂,有了在风雪中也要灿烂活着的、最美的样子。
武昌湖观鸟
千亩湖面如镜,万只候鸟翔集,在望江武昌湖,我看见了人与自然最动人的约定。
破晓的晨光如薄纱般铺在武昌湖面上,我悄悄隐藏在观鸟台的芦苇丛中。突然,一群苍鹭舒展着灰白色的羽翼从头顶掠过,优雅的身姿在初升的阳光下划出流畅的弧线。远处,几只凤头䴙䴘带着幼鸟在碧波间灵活穿梭,泛起圈圈涟漪——武昌湖的一天,就在这生机勃勃的画面中开启了。
1、千年雷池,今日鸟境
“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古训,让望江的这片水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今日的武昌湖,早已从军事禁地蜕变成了生命的乐园。
那块静静伫立的“古雷池”石碑,如今与现代化的观景台相映成趣。古朴的雷池亭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而湖畔新设的生态观鸟站则彰显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古今交融的景象,恰如武昌湖本身的蜕变——既保留了文化记忆,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站在观鸟台上,放眼望去,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水雉踩着浮叶轻盈漫步,其优雅的姿态宛如水上的舞者。偶尔有南归的大雁成群飞过,它们时而在湖面游弋,时而展翅高飞,壮观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如今的武昌湖,既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地标,更是水鸟栖息的生态乐园。这片曾经的金戈铁马之地,如今回荡着的只有鸟儿的鸣唱和游人的轻声赞叹。
2、水上精灵,生态指标
在武昌湖观察得越久,就越能领略到这片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之美。
根据最新的调查,武昌湖湿地共记录到越冬水鸟35种,总数达27600只。其中包括IUCN受胁物种9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4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种。这些数字背后,是武昌湖生态系统健康的明证。
约90%的越冬水鸟和绝大多数濒危保护鸟类均分布在下湖区。分析其原因,是菰的大量生长为水鸟越冬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安全的栖息场所。
在我观察的过程中,一群水雉的到来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被称为“水上凤凰”的珍稀鸟类,在荷叶间轻盈跳跃,它们黑褐相间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水雉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它们的到来,本身就是对武昌湖生态环境的最高评价。
3、四季轮回,鸟语不绝
武昌湖的观鸟之旅,四季各有其独特的韵味。
春秋两季,候鸟迁徙的壮观景象在此上演。成千上万的候鸟在此停歇、补给,湖面上密密麻麻的水鸟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画卷。
冬季的武昌湖则成为了南归大雁的乐园。它们从遥远的北方飞来,选择在这片水域停留,因为这里“丰富的鱼虾资源、适宜的气候条件和大片的浅滩湿地,为大雁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栖息之所”。
夏季,则是繁殖鸟类的天堂。凤头䴙䴘带着它们的孩子在湖面游弋,水雉在荷花丛中筑巢繁殖。整个湖泊充满了新生命的喜悦与活力。
记得前年二月,我在武昌湖湿地见证了候鸟归来的盛况。大批候鸟如约归来,在浅滩觅食休憩,在湖光山色间翱翔,在晚霞的映照下,宛如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4、人鸟共生,和谐之道
在武昌湖观鸟,最令人感动的不仅是鸟类的多样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实践。
当地的生态保护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保护湿地植被、控制水体污染、设立保护区等一系列措施,武昌湖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这些努力为水雉等珍稀物种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家园。
在观鸟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安徽省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他们定期对武昌湖的水鸟进行调查,以准确评价武昌湖作为水鸟越冬地的保护价值。这些科学监测数据,为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附近的居民也逐渐形成了爱鸟护鸟的意识。他们在湖畔休闲散步时,会自觉地保持安静,不打扰这些可爱的精灵。这种人与鸟类的默契,构成了一幅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夕阳西下,我结束了一天的观鸟之旅。回望武昌湖,晚霞将水面染成金黄,一群大雁正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
这片千年雷池,如今已成了候鸟的“天堂”。每一次翅膀的扇动,都是对望江生态保护工作最有力的肯定;每一声鸟儿的鸣唱,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赞美。
离别的路上,我不禁想起那位野生动物监测人员的话:“鸟类的选择,就是生态环境最公正的评分表。”在望江武昌湖,我看到了这份评分的答案——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