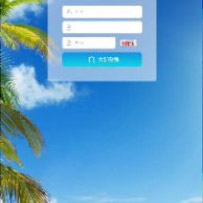那远去的夏日时光
夏天是一年中最受孩子们喜欢的季节。
即便有些人白天要受满身痱子的芒刺蜇疼,晚上要接受蚊虫的侵袭,可夏天对于孩子们的好,真的是全方位的。
白天,菜园里有各种瓜果可以食用,不管是自家的或者别人家的,顺到手上的都是自己的。各种能到手的食物,囫囵吃下去,小肚子涨得溜圆。要是赶上午后时分,大人们都在家歇暑,孩子们便相邀着到长江边洗澡。家乡人把戏水或游泳叫成洗澡。
每天午后,成群结对的孩子穿着裤头往江边进发。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家里酷热难当,门口的树荫下也是热不可支,即便如此,蒲扇作为家里的降温设备,也不是人手一把。只能优先给大人使用,因为,他们白天还得到地里干活,中午回家吃饭休息的时间段,必须要得到充分的保证。
大人们太辛苦,自然也没精力去管孩子,尽管他们知道,在长江里边洗澡非常危险,好在大多数孩子都知道危险。水性好的,围绕着趸船跳水、游泳,不会游的,就在趸船围出来的很小区域里嬉戏。
有人把泥涂抹在自己身上,有人用泥巴打着水战,有人趴在岸边,用脚在水里有序地击打着,身体慢慢地往水里滑溜,不一会儿,可能就浮在水面上了。在江里学游泳更容易一些,说是江水浮力大。
大点的孩子都是穿着裤头下水的,不像年纪小的,他们把裤头脱在岸上,光屁股下水,他们怕家里人通过他的湿裤头而责罚他。
玩够了,小孩子起身上岸,套上裤头就可以回家了。而大孩子不行,他们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将湿裤头拧干水份,然后走到趸船边,一屁股坐到滚烫的船甲板上,或者前面贴在甲板上,甲板像烙铁一样,可焙干裤头的效果特别好。
当他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其实,大人们都知道孩子中午出去干嘛了。为了证明孩子出去洗澡了,父母让孩子伸出胳膊,在上面轻轻地挠一下,胳膊上随即出现了两条白印。这时候,自然少不了一顿“杨树条煮面(挨打)”。父母其实也不是存心要打孩子,主要还是希望能引起孩子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
孩子们也学聪明了,为了让父母挠不出痕,他们洗澡后,再弄出满身大汗,那就再也不出痕了,大夏天的,出汗是最容易的事。
当檐下的日光伸出一米多长的时候,又到了父母们该上工的日子了。他们出门之前,还是要对孩子们叮嘱一番,不要出去玩水,水里有水猴子;在家做一些家务事,等晚上父母收工回家,孩子们在家要把粥煮好,当然,还得把鸡猪喂好。
中午在外面玩得太累了,父母出去后,孩子们还会拿出塑料布或者简易的凉席,要么铺在家里的地上,或者是树荫下的地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天热的日子,人躺在地上,身上出了一身透汗后,身体很快就发软,即便树上的知鸟把天都叫裂了,一点也不影响瞌睡上身的孩子。即便有蚂蚁上身,他们丝毫也感受不到。
当阴凉快要覆盖到整个屋基的时候,孩子们开始活动了。女孩子开始淘米生炉子,用吊罐煮一锅白粥,并在厨房里炒两碗咸菜,这就是一家人的晚餐。力气大的男孩子,自己到井里挑水洒到门前的地上,以便给门口降温,力气小的孩子,两两抬着一桶水,把家里的水缸灌满,以便晚上家里人洗澡用。
天快擦黑的时候,大人们都收工了。拿着毛巾到水塘边简单洗漱,就坐到凉床前的凳子上,孩子们早已给他们盛好了大碗粥在一边晾着。白粥就咸菜,家家户户如此,年年月月不变。
有风的日子,外面的蚊子应该还是有数的,一旦风停了,蚊子便出现了。讲究的人家点上买来的盘香,在上风口点上。舍不得的,一般就在凉床边点一堆碎草,以草的浓烟熏走蚊子,大多数时候,蚊子好像还没反应,人受不了。
一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一家人躺在外面的凉床上、椅子上、凳子上,大人说着稀奇古怪的故事,或者是,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寻找牛郎织女星。那时候,我一直奇怪一个问题,天上的银河就在我们家乡的上空,为什么其他地方的人也会说天河配的故事。甚至在中学地理书上,还出现了银河系和牵牛星座的词汇。
宁静属于白天在地里干活的大人,以及那些还不允许独自往外跑的孩子,青少年的夏夜十分热闹。趁着天黑,他们会打着手电去池塘边抓青蛙、钓黄鳝。天黑之后的青蛙静静地蹲在岸边吃蚊子或者飞蛾,它们已经失去了白天的警醒,即便手电光照在它的身上,它也没有丝毫的反应,然后,一只手从空而降,青蛙只能在手掌下挣扎。
天黑之前,小伙子们把黄鳝卡子放到水中,晚上,打着手电逐个查看卡子上的收获。黄鳝没有鱼那么聪明,见到诱饵都是囫囵一口,诱饵刚吞到嗓子眼,针就刺穿了它的喉咙,即便它还用尽力气在水里纠缠,终究无法摆脱口中的尼龙线的束缚。很多时候,黄鳝还没有咬钩之前,小鱼将针上的饵料都吃掉了,只好再补上饵料,静等下次机会。一个晚上可以无数次查看收获情况。那时候,池塘里野生的东西比较多,一条黄鳝一斤多也是常见的。
尽管知道,晚上辛苦一下,一家人第二天就有美味的青蛙或者鳝鱼吃,可父母亲一直不同意我们晚上去做这些事,一者怕被蛇虫咬,再者也怕意外落水,第三怕我们遇到不干净的东西,那时候,农村人比较迷信,都喜欢传说一些无中生有的故事。即便离家这么多年,我还是害怕当年听到的鬼故事。
我们家人口多,可供在外面乘凉的设备不够。先前,父母亲都是让我们几个小孩子优先使用,他们只是摇着蒲扇静静地坐在一边,等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再回到炙烤了一天的屋里睡觉。
我们兄弟稍大一点之后,晚上,我们便拎着一张草席,到码头上,找块平整些的水泥地上,就地铺上席子,享受着江面上吹来的微风,数着天上的星星,等最后一班客船离开后,便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故乡是男人嵌在基因的密码
思乡,可能是基因里的密码,跟性别有关系。男性和女性思乡之情可能是不一样的。
两千年前,当西楚霸王推翻了强秦的统治政权之后,他立即做出一个决定,穿着漂亮的衣服荣归故里。有人质疑项羽的行为,项羽解释道,富贵不还乡,等于锦衣夜行。不能说项羽的思考不对,人嘛,只有回乡显摆了,才算是光宗耀祖。也许因为后来项羽的失败,对于项羽的行为,后人又创造了一个词汇“沐猴而冠”,说项羽的急功近利行为,仿佛给一只猴子洗完澡后戴上高高的帽子。
谁能知道,项羽当年为什么要回故乡呢?
过了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夺得天下政权之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在自己的故乡安徽凤阳盖一座皇城,甚至还有将首都定在凤阳的想法,最后经高人指点及再三权衡,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上述所说的两个案例都是男人中的豪杰,故乡在他们的心里都是如此的厚重,别说一般老百姓,对于所有男儿,故乡应该是心里最软的所在,故乡是埋得最深的思念。对于作家来说,很多人虽然在故乡逗留的时间很短,可他一辈子能写的都是故乡。由是,思念大多只呈现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好像女性作家都喜欢写外面的世界。
在故乡的时候,脑子里总镌刻着这样一副场景。
当男方挑着礼担,放着鞭炮,敲打着锣鼓,来到女方家接亲的时候,无论女人是多么的不愿意,当吉时已到,她都要在哥哥或者弟弟的背负下,跨出大门,在她的脚即将落地之前,她将手中握着的一把筷子奋力地向身后甩出去。
在浓烈的鞭炮和震天锣鼓的簇拥下,她被两个小姑娘搀扶着,快速地跑向男人的家,那是一段多么艰难的旅程呢,她从熟悉跑向未知,从亲人身边跑向陌生的远方。那把扔回来的筷子,以及她不能转身的步伐,都坚定地说明,她真的如古人说的,此刻,她已经成为“泼出去的水”,几乎不能再回头了。
我一直不知道女人的心思。
那是多么恐怖的事啊,当盖头掀开之后,眼前呈现的是完全陌生的世界。盖头盖上前,身边都是亲人,盖头把亲人都给隐藏了,身边现在都是陌生人,这是她要面对的世界,余生她要完全融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要把这些陌生人一个个地培养成亲人,那是多么艰难的历程!
当然,我能想到的仅仅是民间女子,放眼到官家,那些女子的命运似乎更加悲惨。
她们是被当着美人被人认领,然后是带着使命走向一个完全未知的远方。离开宫城之前,她还锦衣玉食,可一旦走出城廓,周遭就是大漠孤烟、黄沙漫道,最要命的是,身边围着的是长相稀奇古怪,甚至语言都不相通的人。胡天八月即进入雪季,草原、大漠、飞雪、流沙,她不是在嫁人,而是在走向死亡。
身边搁置的琵琶,先前可能是美人的点缀,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忠实的知音,只有对着琵琶才能说出心中的委屈和恐惧。草原原来越宽广,而她的心越走越黑暗。她不是走向明天,而是在走向焦虑、担心和彷徨。
假如她能有选择的机会,你猜她会做出什么决定呢?十有八九,她会勇往直前,因为,她知道,往前走才是她的宿命,未知才是女人的归宿。
相对于和亲到漠北的王昭君,大唐盛世的文成公主西行的心境会轻松一些,因为她走之前还带了很多汉地的种子、物资,她想把遥远的西域变成家乡的样子。这不仅包括物品,甚至包括信仰,她带走了世界上唯一的释迦摩尼十二岁等身相,她要以虔诚教化那些处于蒙昧地界的人。
文成公主没有像乡下女那样往回扔一把筷子,据说那是禁止女人回头的誓言,文成公主丢下了她的梳子、镜子等随身物品,它们就地化成了日月山和倒淌河,也许她是无心的,也有可能是存心的,她也怕一去之后,家乡人便淡忘了对她的念想。她是在沿途标记行走的轨迹吗?
从大唐盛世到现在,时光过去了1400年,雪域高原上还在流传着文成公主的传说,这足以说明,她不仅融进了那座新家,而且在家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雪域高原缺氧,但是不缺信仰,文成公主也许没有得到男女之爱,但是她得到了高原上千余年来子民的爱,那份爱飞过崇山峻岭,爱传了百年千年。
记得当年送姐姐走的时候我没哭,可我这个“送郎舅”跟姐姐告别的时候流泪了,我不是舍不得,而是莫名的焦虑,我根本想象不到姐姐在那儿的适应方式。当年我不知道,也许那一刻,对于女人来说才是生命的真正开始呢。
故乡是男人始终迈不过的情感软肋。
无论是帝王将相,或者是贩夫走卒、平头百姓,故乡始终是男人割舍不掉的羁绊,假如没有故乡,男人好像永远无法活得圆满,生命似乎都无法闭环。即便故乡是个点,可也是凝聚一生情感的起点和支点,没有了故乡,情感就无依无着。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贺知章在寻根吗?树高千丈,他还是沿着生命的指引回来了。现在读起来这不是诗,而是在解答人生的哲学命题。
我是谁,我不过是故乡的一个游子,我从故乡走出来,现在又回到了故乡去。这个哲学三问很圆满。之所以遵从这样的轨迹,因为,我的基因里嵌了故乡的密码。
那刻在心底的熟悉与陌生
高铁列车快速地穿行,即便昏昏欲睡,可眼睛还是被窗外的绿吸引着。
盛夏的江淮大地,满眼都是绿色,即便是先前泛着潋滟波纹的水塘,此刻也被绿色的荷叶覆盖了起来。
即便如此,还是水里稀稀拉拉的绿秧苗,因为过于瘦弱而无法掩盖住周围的水光,我知道那是新插下去的稻秧,我也感到很庆幸,能在立秋之前,将秧苗插到田里,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呢。
田野里没有人的影子,可我还是从没有直起来的嫩苗中看到人群刚刚散去的痕迹。那之前,是多么紧张的劳动场景呢。
也就在半个月前,男人在夜里拿出放置了一段时间的镰刀,趁着夜色下的月光将全部的刀具磨得精薄的白色,不时地,他们会停下来,用拇指在刀刃上轻刮着,目的是为了验证刀口的锐利程度。
士兵们战前是枕戈待旦,这些男人似乎已经开始枕刀待旦。不对,其实,他们已经等不到天明就准备出发了,因为,他们要趁凉去把田里接近熟透的稻子给割回来。
为了节省第二天的时间,女人们整个晚上都无法入睡了,因为她要在夜里把第二天下田的人的饭菜准备好。所有人都要早早地吃饭,以便能赶在天不亮之前就能干起来。
来到田间地头,选好了下刀的方向之后,所有的人都挽起裤脚,弯腰下刀,刀子刷刷地挥动起来,不一会儿,身后便倒覆一片散发着草香味的稻杆。下手快的人,不割完一垄几乎不会直腰。即便能直起腰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坚持,他们知道,一旦站起身,腰一次比一次难弯下去。腰一直弯着,直到极度劳累让腰有了塌陷之感,进而失去知觉,才能保证最后无需弯腰。
估摸着,剩下的稻子能由女人和孩子完成了,男人才放下镰刀,开始将货桶拖到田里,那是一只由厚木料做成的容器,新割下的稻子,由男人倒拎着,用力地朝着货桶壁上摔打,以便将稻穗敲到货桶里。
“砰砰砰”的击打声,能传出一里多地。那是一幅力量与美的尽情绽放画面,可惜,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用心思去欣赏,大家都忙着自己的活。年幼的孩子不停地拾起先前放在地上的稻铺,不停地递到货桶前的男人手上,以便男人集中精力打着稻子。
不一会儿功夫,货桶里面就盛了半下稻粒。有人开始用麻袋装稻子,满满一袋子稻子,被人架到力气大的男人肩头上,由他蹚着稻田里的泥浆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背负到平板车可以到达的路上。
太阳出来后,立即对皮肤形成炙烤感,忙碌的人几乎顾及不了这些,即便脚上盯了蚂蟥,看着腿上流血,立即伸出手掌对蚂蟥身上拍打几下,受痛的蚂蟥蜷缩着掉落下来,为了防止它二次伤害,男人从田埂上摘取一根灌木枝,将蚂蟥穿着翻过来插到田埂上暴晒,据说只有这样,才能让蚂蟥真正地死掉。
蚂蟥吸出来的血还在流淌,从水田里招点水冲洗一下,要是血流不止,就从田埂上随便揪片树叶贴在出血处,权当止血了。随后立即投入到工作中,接近中午的时候,太阳能把人热得炸裂,脚下的水都被烤得发烫,以至于从下往上熏蒸人的身体。
无论多么艰难,大人总得不停地坚持着,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活必须尽快完成。可孩子们想不到这些,他们趁机会躲到田埂上不太成才的树荫下,那地方似乎是世界上最凉快的地方,哪怕只能躲个片刻,感觉也算是重生了一次。
经过几个烈日下的暴晒和劳碌,早稻被弄回到家里,可这还不算完,因为,接下来的任务会更重。农人必须在短短的几天里,把新割完的田地耕耘一遍,以便尽快收拾好田垄,将晚稻秧插下去。虽然犁地和插秧看似没有割稻子那么繁重,可那也是极费体力的事,毕竟已经劳作多日,身体快撑不住了。
这个时候的农民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他们害怕天热,因为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做这样的体力劳动非常痛苦,可这时候,他们更害怕下雨,因为新割下来的稻子,只有晴天才能很快晒干,要是遇到雨,会导致潮湿的稻子发芽。可要是不下雨,稻子割完后,犁田和耘田是非常困难的事,田里没水,秧苗无法存活。
每个在江淮地区做过农活的人都知道这个折磨人的场景,它们拥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双抢”,即抢种抢收,虽然工作量巨大,但是他们必须在立秋前的半个月内全部完成。那些年,不时传来某地有人永远倒在田埂上的事。
眼下离立秋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看着那水中轻轻摇曳的嫩苗,真的为这么早就顺利完成“双抢”的农人感到庆幸,他们顺利地度过了今年中最艰难的时刻,余下的日子就等着丰收的喜悦了,即便后面还要付出无尽的劳作。
家乡稻子碾出的米其实不好吃,可当年它是我们生活和生存的根本。不知道现在的稻子是否为新品种,但愿它能带来更好的口感和更丰足的营养,或者它能减轻乡亲的劳作量,让农民的负担能轻些,或更轻一些。
我知道先前为什么不喜欢深绿色了,那是劳作的颜色,是被生命驱赶着奔跑的颜色,绿色是忙碌的颜色,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可绿色又是生命的颜色,只有绿色才能遇见金黄的秋色。
高铁还在快速地奔跑,我用手机尽情地记录着。我记着的好像不仅仅是绿色,更是回忆着那刻在心底的熟悉和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