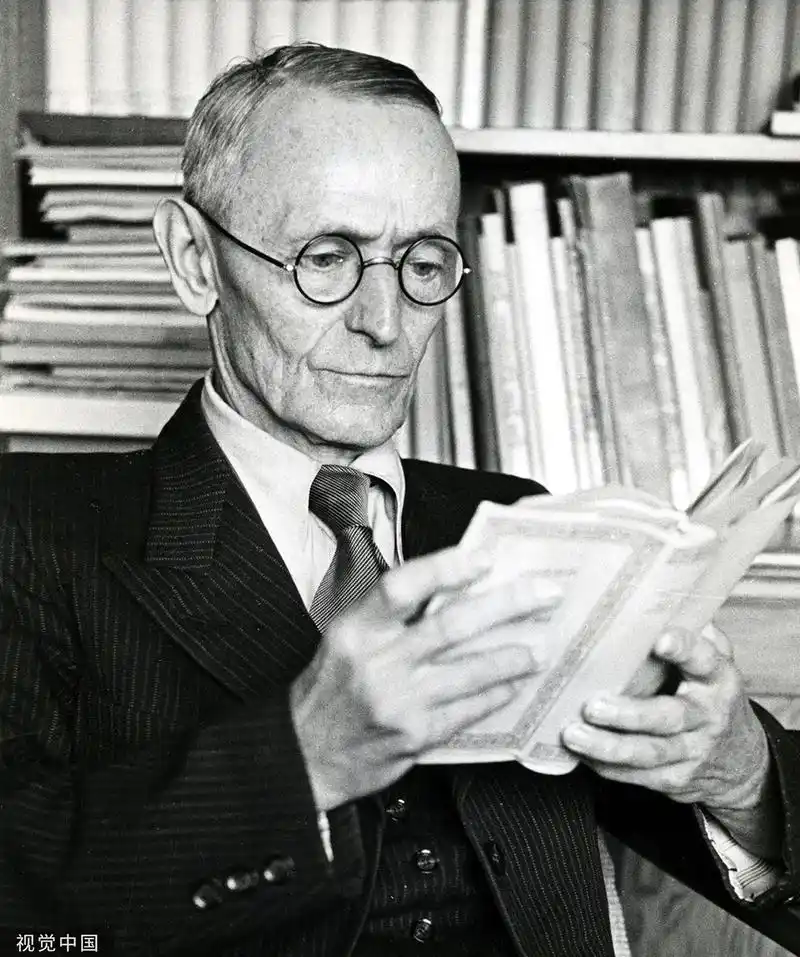乙巳年春日早上,木空老突然微信我,“画说红楼梦你要吗?”我一愣,回了两字:书吗?
那边很快拍图发过来,原来是他的书《画说红楼梦》印出来了,这真值得祝贺。
木空老画《红楼梦》的事,多年前媒体有过报道,但我那时并没看到。2005年,他因为画长卷《合肥昔景》上过一次报纸;一年后,又因为画十八米长卷《合肥环城翡翠》而被报道。三年后,《画说红楼梦》208幅作品完成,复又惊动媒体一次。但上述几次报道,因并未见诸我所在媒体,所以不知道他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他却说,他和我是“三十年的书友”,微信上这样说,那天去他住处拿《画说红楼梦》时,他也是这样写,“卅年前书友”。他说他在三十年前来报社找王丽萍,要找戴厚英的相关报道,王丽萍不在,是我接待的,我还给他看了合订本。老人家的这个回忆,应该是错把别人当成我了。因为我和王丽萍那时候并不在一幢楼里办公,我在晚报社,她在日报社。所以木空老的这个回忆,我在记忆库里,是怎么都找不到半点印象的;而我记忆中的认识他,是在另一个场景。
2014年4月2日,我和台湾《联合报》老记者吴心白合著的《白马集》印了出来,那一天,88岁的心白老从台北飞深圳,他此行专为此书而来。4日中午,飞抵合肥,我去机场接他。6日下午,刘政屏先生在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四楼,为此书策划了一个活动,名之为“两岸文学民间交流会”,活动开始前,画家高军突然现身,他带着一位居士过来,便是此年71岁的木空老,我好奇于他的身份,便在高军的介绍下,互加了联系方式。
高军当时正在写一本奇特的书,写画坛那些奇闻逸事,而这些故事多与老合肥有关,木空老显然是一位能走动的“活掌故”,他知道这个城里几十年前发生的很多事情,他家虽非高门大族,却也是大户人家,何况他又从小染指丹青,认识这个城里的很多画家,他本人经历也算奇特,画画、玩鸟、玩丝竹,出世而又入世,在社会的边缘上生存,又在庙宇中居住过多年,要写古怪的书,访谈对象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呢?
木空老画古城画自己的故家,亦是故事多多,而这些,恰恰也是媒体人关心的。
认识不久后,木空老便来编辑部里找我来了。具体的情形我已记不得,只知道他当时正苦于如何把他的随笔小集《浮生梦影》,从稿本变成印刷品。我便帮他找了我的同事帮忙,让她在工作之余,把那些文稿录入到电脑里,然后让他拷走。不久后,这本簿簿的小书就印了出来,送了我一本。许是没人校对也乏人编辑的缘故,小书中的错误实有不少,印得也有些粗糙,可就这样一本粗糙的印刷物,在我多年后扔出去很多不要的书时,它却始终留在我的书架上,我每每翻到,还会读它一读,十余年来,我看它,至少也有三回了。
值得我看上三回的书,是少之又少的。
很多书自从请进家门,有不少连一回都没看完,便被弃于一边,更何况是三回呢。
这本小书值得留下来,思量起来原因总有几个,一是因它是本小书,容量小,不占地方,百余页笔记本大小,只消花个半天就能看完,这就是小书的可爱之处。类似的小书还有几本,无非来路各有不同,比如某位画家的京漂故事,我也一直收藏着,这是其一;其二是,里面写的他的家族史,个人史,都和合肥这座古老的城池有些关联,所以文本虽然粗糙了一些,但内里自有其光芒在;其三,作为一个体制外画家,木空老长达五十余年的绘画史,虽艰辛艰难多有坎坷,却屡屡画出体制内画家画不了的大作、长卷,比如他顷八年之力画《红楼梦》,乃安徽独一人;他画他记忆中的《合肥昔景》,也是独一个。这种众人不画他独画的风格,正是我钦敬他的地方。他还敢说敢写。六零年代他当过六年兵,转业后在工厂里做工人,因倔犟而刚直,不讨领导欢喜,工作中便被屡屡穿小鞋。后来虽然在橱窗设计中获过大奖,但获奖归来却被领导“贬”去做木匠,所以他戏称自己是“木画师”,而木空这一僧名的由来,亦和其做木匠这段经历有关。
木空老,大名张国瑞,1943年生人。他这个张,和合肥张家四姐妹的那个张,是有些关联的,至少他们的远祖都来自江西同一人,无非落户合肥后,分枝散叶属于不同的支脉而已。
在《浮声梦影》扉页上,他写了赠我的时间是“2014.5.22”,可见这本书的问世,就是《白马集》见面后不久的事。他为了酬谢录入者,托我送了画给她,也送了画给我。
然后即此别过,又是多年不见。
这本小书的序非常短小,以许有为先生写的一首《古风赠木空居士张国瑞》作序。诗云:
国瑞先生擅丹青,开福古刹潜修行;
闲云野鹤甘自守,兴来泼墨绘彩屏。
庐州风物笔底走,百尺长卷惊古城;
妙公上人重才俊,赐君雅号曰半僧。
半僧虔诚佛弟子,木空居士其嘉名;
愧我红尘槛内客,半生蹭蹭无所成。
木空是我槛外友,槛内何妨啖荤腥;
君子之闪淡如水,方内方外皆可名。
这首古风诗写得实在是好,诗写出来后,许先生委托同是张家的画家张以永书之,故其诗中跋语为:
己丑清秋燕居,忽念及方外友人国瑞潜修于山中,闪念间大有“雪夜访戴”之思。诗兴泉涌。旋即命笔占古风一首,倩以永贤弟台捉刀书之,聊以补壁耳。
己丑年,应是1985年。而木空老为这本小书写的自序,写于2011年的2月。序中曰:
余自幼受庭训,酷爱涂鸦;童年遭战火,年少遇饥荒,而立逢文革,一事无成。然不惑之年欣闻佛法,皈依三宝,花甲又剃度为妙安长老关门弟子。长住开福禅寺,茹素念佛,闭门读书,潜心作画,喜结善缘。弹指挥间,年来虚度二万一千六百日,大半沉酣于花鸟虫鱼之间。
沉沦丹青五十余年,顽固不化,孤芳自赏,穷困潦倒,但承蒙看客厚爱,知音夸讲,乃至各媒体宣传报导。拙作被世界各地爱好者收藏并被有关机构聘为画师、教授、会长等,实在惭愧,免提。终将以作品为准,勿误!
这短序写得不差吧?自序的最后还有其小诗一首以自嘲:
生来自负懒求人,不惯逢迎受折磨;
人事诗剑两蹉跎,引颈吟风自唱歌。
木空老的性格、经历和遭遇,在这篇短序及诗里已多多少少做了交待。
那天带朋友去他住处,问他那本小书可还有?他说没了,早给光了。
三四年前他在微信里说,除《浮声梦影》外,他还写有《寺中随笔》和《炉中日记》(部队日记),他想把三书合成一本印出来,可忽忽数年过去,他期待中的这本书还只是一个梦而已,并未做成。而这本《画说红楼梦》,他花八年时间画它,要印出来也是其难无比,他找过很多人帮忙,最后才印了三百本出来,印刷费3万块钱是他自己出的。他的退休工资,从刚退休时的一百多,加到现在,总算加到三千多,所以印行这本书也是诸多不易。他说不是谁向他讨书他都给。
画红楼梦时他还住在寺庙里,画到一半时他离开了,在外找地方租住,名之曰“一张画室”,可见其小。后来的住处也是别人提供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小屋一间花鸟虫鱼,书画丝竹样样有”,闲时听听鸟语,吹吹丝竹,在小画桌上铺纸画画,写点小字,算是其乐。
他的小屋在视频中我已无比熟悉,那天终于见到了。
也就十来平的小屋带一个东阳台,门楣上方贴着“苟奋轩”三字,为其手笔,显见是其斋名。窗台上方挂着2005年端阳日迁新居时写的“九久小舍”四字,果然是小舍,内里却丰富极了。集画室、居室、花鸟虫鱼室于一体。老照片、作品则散布四周。门上亦张贴着画。小而窄的小舍里,满满当当,却也丰富无比。而他那些被媒体报道过的珍贵画作,大多放在一个有年头的木箱里。17岁时画的《岁朝图》应该是他的处女作,精裱后挂在床头上方,尤其令人震撼的是他凭记忆画出的童年故居《仓塘老屋》,挂在小屋的东南边,抬头一望,便可见合肥旧时风景扑面而来,画中他的故居里有花园,有依依垂柳,有房屋数幢,旧房数十间,邻包河,邻老城池东门,且来看其跋语:
仓塘老屋。童年故居。木空于二0一九年二月二十七忆写。老居又称合肥小南园,祖父创业,位合肥东南城墙脚下,与洪家花园毗邻。一九三八年合肥沦陷,老屋被日军司令部占用,一九四五年胜利又被国民党占用,四九年合肥解放,小南园又是安徽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地,一九五三年成立中共省委,老屋被征收,全家搬迁,直至文化大革命,老屋仍存一路,后拆除建高楼,为省委宿舍。木空又记。
这段跋语我一字一句录入,内心有点小小波荡,木空老凭记忆画出他小时居住过的小南园,该是何种心情?而他临老,却在城里并无一屋,又是何种心情?读者诸君自可理解。故其在《浮生梦影》的封面下自署“木空(南园旧友)”。七十年前的合肥小南园,现在的合肥人多已茫无所知,我亦如此,旧居的风华也只有梦里去寻,画里绘出,方能了然。
这一天,画说红楼梦的原作我也看到了。木空老自己亲自裱好,装祯好,封面也是自己设计的。七十年代百货大楼的橱窗设计师,差点要被影院调入做电影海报设计的木画师,这些技艺,只是随身携带的小玩艺而已。
为何画红楼梦呢?
因为熟啊,这本书他读过至少五六遍。有些章节,也许读的次数更多。
年少时,母亲就讲红楼梦的故事给他听,他们家还有红楼梦的老版本。他母亲是大家闺秀,床头上就放着宋词书。父亲也是读书人。祖父是创业的老板,小南园就是他置下的。李鸿章故居对面,有一经营杂货兼批发零售的商铺,名张同裕,曾经是合肥的老字号,便是其祖父张日春肩扛手提白手起家创下的家业。可其祖父不知得罪了何人,在1938年初合肥沦陷前夕的小年夜里不幸遇害,此案八十余年,至今未破。此后的张家,则只有旧梦可寻。
木空老在孤独时看红楼梦,在无聊时看红楼梦,在痛苦时看红楼梦,他说红楼梦就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全写到了,看看红楼梦也就够了。他的读书也就痴迷这一部。
画红楼梦是一稿成,还是要画几次一改再改呢?朋友风忍不住发问了。
木空老似不屑回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画画要有激情啊,没有激情是画不出来的。激情到了,自然一稿成。
风不是画家,只是一位热情的写作者。和我一样,也曾经是纸媒的编辑。她曾经呆过的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过木空老,可她居然,也无有印象。
我说这些画作可以捐出去。捐给美术馆博物馆,我认识的不少老画家,现在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把作品捐到美术馆去。我还居间联系, 让老作家石楠先生捐画给安徽省美术馆,这事后来办成了。
可木空老说,捐给谁呢?官家可要?要了后弃之一边他又该如何?的确是个问题。
他说起黄宾虹死前把所有的画作都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结果呢,被丢在地下仓库里无人问津,直到几十年后,这批作品才被“发现”。这是他不愿意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