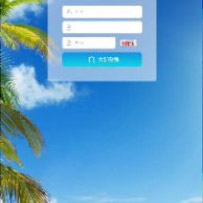春节刚过,老家的大妹妹打来电话,告之我,她九十七岁的婆婆去世了。在我们老家,丧葬仪式极为隆重,而“摆祭”更是其中的重头戏。妹妹在电话里简单地说:“就电话里说一下,不专门‘把信’了。”然而,我知道,这绝非小事。
在我们老家,对先人去世的礼数有着严格的规定。亲人去世后,要请风水先生依据逝者的生辰八字及去世时的八字,结合至亲的八字测算出出殡和下葬的时辰。随后,负责丧事的主事者会安排人到丧事主家的各亲戚家通报丧事的一切事宜和时间,以便各亲戚前来悼念。这叫“把信”。一般是出殡的前一天去悼念逝者,这种集中拜祭逝者的仪式,叫做“摆祭”。“摆祭”不仅是对逝者的悼念和怀念,也是对逝者亲属的精神慰藉,更是亲戚朋友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因此,“摆祭”是乡风民俗中一件讲究仪式感且非常隆重的事。
接到电话后,我马上问清楚“摆祭”的日期,决定提前一天赶回去。妹妹迅速告知了具体时间,这关乎娘家的面子。她不时打电话问我上车没有,生怕我因来南京不久,怕麻烦而用微信转账礼金了事。得知我上车后,她又不停问我到了哪里,说要安排车子来接,晚上和哥哥一起到她家吃晚饭,这样可以省得烧火做饭。我理解妹妹的心情,电话里告诉她:“你家正忙,我乘便车回家,晚上去你家吃晚饭。”
我和哥哥从不同的方向赶回家后,马上开始准备第二天“摆祭”的事宜。花圈、斗香、柴、米、香纸、爆竹,一样都不能少,礼金不求高,但绝不能缺。我们还请了本房族的兄弟帮忙,并挑选了几个会打锣鼓的人,负责在第二天打出好听的调子。
这种讲究礼数的事,分寸必须把握好。我们等到老先生的娘家摆祭的人到过之后才出发。接近妹妹家时,锣鼓喧天,烟花爆竹齐响。对方也敲锣打鼓,燃放烟花爆竹迎接。老先生的孝子孝孙跪地迎接,还有数个戴红孝帽的玄孙辈掺杂其中。我们刚到过后,另一班摆祭的人又至,远处路上还传来了摆祭的锣鼓声。接担、回礼、祭拜,主事者安排得井井有条,帮忙的人各司其职。
从人们的议论中,我得知去世的老先生有四个娘家。老先生出生的年代,生活条件艰苦,尤其是女孩,生活环境更差,将女孩送给人家养或做童养媳是很普遍的事。主事者咨询看风水的老先生:“四个娘家哪家为大,酒桌怎么摆?”看风水的老先生回答:“生的娘家放一边,养的娘家大似天,养的娘家在哪出嫁,哪家为大。”传统的礼数总能说出个道道来。
老先生九十七岁,子孙众多,亲戚朋友也多。来摆祭的有十几班锣鼓,加上零零散散祭拜的人,摆了二十桌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帮忙了,有些刚出去打工的人也赶回家帮忙。虽然是丧事,但在乡村也属于“白喜事”,场景很是热闹。这几年乡村的生活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明节回家祭祖的人似乎比春节回家过年的人还多;过年可以把长辈接到工作的地方团圆,但祭祖却必须到先人安息的地方。参与白事的人比参与红喜事的人多,红喜事不请可不来,白事却是不请自来。
乡村并不因冷落而丧失传统文化的土壤。我很享受乡村这种氛围,每次回家都像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还有地里顽强生长的麦苗和河边逢春吐绿的柳树,构成了一幅充满乡村气息的画面。每次回家,我都喜欢在田间地坝上走一走。如今物质丰富,却少有人关注这片土地的效益。然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每年两会上都将粮食总产量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指标,每年秋收之时,央视都会着重播出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因为这是给这个人口大国所有人吃下最重要的一颗定心丸。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在传承着古老的民风民俗。虽然这些民风民俗并不是什么高大上,但从这些民风民俗中演绎出来的文明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文明文化,才是能与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相抗衡的文明文化。百十年前,费孝通先生所言的文化自觉,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乡村文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乡村,乡村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一些传统习俗在年轻一代中逐渐淡化,甚至被遗忘。这让我深感忧虑。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不能让这颗璀璨的明珠在我们手中黯淡。
乡村文化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加强对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学校可以开设相关课程,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和热爱乡村文化。我们每个人也可以从自身做起,多回家乡走走,参与乡村文化活动,为乡村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承载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凝聚着我们的民族精神。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同守护这片充满诗意的土地,让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