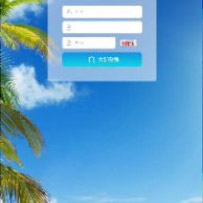身体的疼痛可以让一顿美餐如曹操手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甘。曹操大诗人心有痛事,进退维谷,我又没有他那么大的心痛之事!可此刻,我对此却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深刻。妻子知道我特别喜欢啃红烧猪蹄子,又见我右手肿胀得不能动弹,便为我精心做了一盘,想用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方式缓解一下我的疼痛感。但我的右手无力,也不是无力,而是根本不敢用力,无法用筷子把这么可口的东西顺利地送到嘴里。我于是想着试试左手,从功能上讲,毕竟它是我的另一半。当我试着启动左手时,感觉特别不舒服,不顺畅,基本不在一个跑道上,猪蹄子在那左手的筷子上像小时候钓鱼放在鱼钩上的饵料,我这条鱼想上钩,居然上不了。原来不仅到嘴的肥肉容易跑掉,到嘴的猪蹄子也容易跑掉。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我接着产生了另一种感觉,我即便上了钩,到了嘴里,也肯定仍如曹操手中的鸡肋,弃之?食之?都是怪怪的。也就是说,妻子不是杨修,猜不透我那胃在身体疼痛时是个什么心态,她的分散疗法被我的左手拦腰斩断,所以几乎没有疗效。
人类的身体经过数万年的进化后,功能其实均有大量储备,比如肾脏有两个,失去一个,另一个足以让你继续生存,比如肺有两叶,失去一叶,肯定不影响我们正常呼吸,再比如眼、耳、鼻、手、脚均成双成对,为什么我的一双手肿了一只,另一只手怎么会让我的生活受到如此大的影响呢?感觉进化来的功能在我这里进行了退化,平时熟睡的那部分居然不能及时唤醒。
据说,人类的精神不适可以换算成肉体的疼痛,我想,肉体的疼痛一定也能换算成精神的不适。我感觉我手在疼痛的同时,精神也似有了萎靡不振的样子,自己都觉得自己恍兮惚兮。
妻子说:“至于吗?”我不作答。
人类一直想开发右脑,所以有人故意锻炼左手,甚至一段时间内,对“左撇子”尊敬有加。我这里没有对“左撇子”有不敬之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我亦然,很不习惯用左手。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有人用左手夹菜,如果碰巧我与之为邻,我便有些不适应,觉得他那筷子与我那筷子快要干上一架。从小父亲就教我必须用右手吃饭,并告诉我这是规矩,大家都执行。
使用右手实际是中华这个大家族中的一项文化,或可叫“右文化”。并排站立、行走或者就座的时候,主人总是主动居左,而请客人居右。晚辈应当主动居左,而请长辈居右。职位、身份低者应当主动居左,而请职位、身份高者居右。《史记·田叔列传》就有“无出其右”的成语典故。即便是很多朝代的丞相也多以右丞相为长为尊。
说来也怪,我小时候咋就偏偏用了左手!为此,吃饭的时候没少挨揍,甚至父亲在打我时,不惜连着碗及碗内有时是山芋有时是米饭一起打碎──当然,那被打翻在地上的米饭等于是我吃掉了,因为父亲不会让我再吃了。须知那时粮食金贵到你痛心的程度,买一只碗更非易事,有的人家一家人一人一碗,客人来了要借碗吃饭是常有的事,所以过年时,家家都会买几只新碗,且借来木匠用的金刚凿刻上自家姓氏,以免被借时搞混淆了。那时的生产队甚至从鸡口夺粮,因为农田一般紧挨村庄,所以鸡随时都会跑田里偷啄那还没饱满的稻穗,所以生产队那时有一个职业:看鸡或看麻雀。我偶尔就从事过这个工种,这是个挺快活的职业,没有火热的太阳烘烤。
我想父亲当时就是以这种付出代价的暴露疗法来治疗我的用左手吃饭的毛病(过后他应该心痛吧)。在此我要说明一下,这并非家暴,我父亲也从没有实施过家暴。事实上,那个年代的父辈基本都是用这种方式教育下一代的,且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对此感觉终生受益,甚至有的人看着自己身上那留下来的伤疤,高兴时便笑笑地挠一下,并说早就不痛了,痒痒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有足够的生活韧性经得起各种风雨的冲击,我也因此顺利地学会了用右手生活。
我对开发右脑没有研究,准确地说不是没有研究,而是没那本事进行研究,但此时我很不想锻炼我的左手,可我的右手疼痛。先是试着用筷子,然后改用勺子,但都不顺利。疼痛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情绪。
由于晚上痛得睡不着,便爬起来试着写诗。现在回过头来翻看这些文字:一塌糊涂。有人说疼痛出诗人,我认为有些扯蛋了。人一旦带着某种疼痛去做某件事,情绪自然就不受控,并打开它的闸门。情绪的闸门一旦打开,处在这个航道里的其他东西基本就无路可走了。我写诗过后便什么也没干,包括玩游戏、打牌,包括看书、敲键盘──现在都不叫写字,叫敲键盘,这点比开发右脑容易多了。
有同事笑我,你昨天不是好好的嘛,今天怎么就残了?我说,人很容易残的。不信,你也试试?打趣归打趣,手仍然痛得我龇牙裂嘴,事也就顺便为同事包做了。我左手指挥鼠标就像我指挥我的左手,十分不灵。
世上的事就是怪。妻子说,好好的一个人出去吃一餐饭,喝几滴酒,回得家来,手居然是肿的,还加一脸醉相、一身醉气、一副醉态。总算老天爷开眼,你家祖上有德,没发现有什么骨折与骨裂。妻子一套一套地挖苦我,我自己想着想着也就一脸的难堪,很是后悔。吃过饭直接回家不就什么事没有吗!不就会躲过这一劫了吗!但命中的那个劫,属于你的终究是你的,一定躲不过。我平时总是不信,这回信了。我想,能躲过的肯定都不是劫,或者那劫根本就不属于你。古人造出这个劫字,估计也是因为“在劫难逃”。我的确是没有躲过,就像我下的那盘围棋,输就输那个劫上。
生命脆弱,脆弱到同学S家(我就不直接说了,免得误解)门前一块青苔居然让我再次被打了一劫。孔老夫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我被打一劫后,半月不知肉香。这是反比还是正比?我在想,孔夫子的那个肉香是否也是猪蹄子香呢?我没有找到任何信息证明孔夫子喜欢啃猪蹄子,他老人家周游列国,恐怕没有时间啃。我也没听到韶乐,而是听到了自己“扑通”一声重重地坐在了地上。同学S肯定吓了一大跳,夫妻二人匆匆跑出来,扶我起来,我说,你家门前也不安个路灯?同学调侃我,想不到你临走还行个大礼。我说不行大礼,你们也不出来送我呀!他二人笑归笑,很快便担心起来,因为在他家门前摔倒的,我又喝了酒,年龄也不轻,假如骨折了或摔个脑中风咋办?估计他们担心如果摔出严重问题,他们的责任也就来了。我笑着说没事,我咋是那种人,中风了也是自己摔的,怪本方土地也不能怪你们家。这年头发家致富种什么的都有,你们家不致于中青苔致富吧!
也许是喝了酒,当时真就没什么感觉,右手关节活动起来没什么不适,仅手掌破了点小皮。但到家后就不一样了,酒劲过后,精神松下来后,右手在半夜时分肿胀了起来,凌晨到医院拍片却未见骨折与骨裂,这让妻子心中的石头落下了地,她打趣我,只要没骨折与骨裂,痛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妻子知道我是个天生特别怕痛,且特别不扛痛的人──扛痛一词属我家乡土语,但它太形象了,比之忍痛一词几乎不在一个层面上,比之左思《三都赋》中“翘关找鼎”一词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平时打个小针我都可能咬牙切齿──我是常常宁愿效果差些也要吃药,甚至不论中药还是西药,而不想打针。但越怕痛,痛的机会却总属于我,比如这次同学饮酒临时动议到他家对弈,似遭遇了墨菲定律,手痛得十分厉害,而且越是想转移越是疼痛,以致于有了微微颤抖的迹象。现在想来,有意而为,必防范森严。岂不痛哉?
美国学者凯博文曾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中指出,思维的疾病可以转化为肉体的痛苦,通过肉体的疼痛来释放,让肉体来承担。但我的思维没有疾病呀,与同学一起乘着酒兴,黑白二道对上一局。难不成输上一局棋,就转成了疼痛?凯博文接着说了另一句话:“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问题的解释”。这话此刻如果反向地思考我,就不怎么正确了,因为我将肉体的疼痛转换成思维的不适后,比如不愿看书,不愿敲键盘,甚至就不怎么愿意谈心交流,我的脑子仍始终摆脱不了右手关节带给我的疼痛,也就是说我的疼痛转换成我的思维后,我的思维没有有效地阻止我的疼痛一再发生,他们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甚至密切到了一个闭合状态。
抑或我坐在沙发上翻来覆去是一种调节?我妻子说我这是在蛆拱磨,那疼痛如磨,我这条小蛆怎么能拱走或移动这轮石磨!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十分疼痛,妻子这会子感觉我不见得就是不扛痛,她担心可能另有情况。于是找人开车到乡下找她父亲我的岳父大人。岳父八十多岁了,精神仍然矍铄。他是一名跌打郎中,周围十里八乡,谁歪了脚、扭了腰、脱了臼,都找他。我想乡民们一是看他分文不取,二是图个十分方便,三是他真能把他们这些不慎治好,较之医院,好处甚至还不只这三项。我在他七十岁时就向他提出跟他学这门手艺,但现在他八十多岁了,我却一直未成行。我似乎一直有这么个毛病,做事拖拖拉拉。有次他还调侃我,现在不能怪我了,我可没有封建思想,传男不传女哟,怪只怪你自己不想学了!
我想这可能要成我的终身之痛了。
岳父在摸了摸、掐了掐我的右手后告诉我,我的右手关节骨裂了。我说没有呀,你弄错了没有?我拍了片子呀!他说,再去拍吧。果然,回来后,再找了一家医院,医生告诉我,骨裂了。并告诉我,开始为什么没有拍到,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出现骨裂。目前应该是发展的结果。我想,我也没有再次跌倒呀,怎么就发展了呢?这世界的发展方式也真是千姿百态。
同学S第五天打来了电话,说他一直担心。我当然一直没敢说实情。实情有时是不能随便说的,说了就可能引发误会,甚至伤筋动骨。我说我右手没事,查也查了,看也看了,我正在办公室里忙哟!而彼时我正呲牙咧嘴。几十年的老同学,我不能让我的疼痛转移到他的身上,成为他的疼痛。我说哪天我们再杀一局吧,我得把那么个劫夺回来,打你一劫。
他说,有本事你放马过来吧。我突然发现当我说到打他一劫时,我的右手没怎么痛。
我感到,幻想自己取胜,而别人失败可能是一个转换疼痛的方式。但当放下电话后,我的右手又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