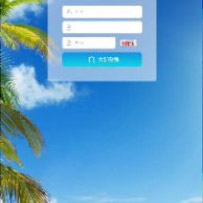在一朵雪花上轮回
大雪那天下了大雪。这是冰心先生说的,也是我祖母说的。我的祖母一生窝在皖东那个浑如一粒豆子的小山村,她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冰心的老人,与自己说过同样浅显而深刻的话。
大雪那天下的雪,不是小雪,更不是虚构的雪。那纷纷扬扬的雪花,不偏不倚地偏偏下在“大雪”节气那一天,深藏其中的秘密,又偏偏被有心的冰心和我的祖母发现了。当然,其他人也经历了那场雪,但是,他们只看到了雪,并未将雪与某种恒久的非物质的东西联系起来。我猜想,这两位老人所说的雪,肯定不是同一场雪,它们一个落在北方,一个落在皖东。但是,肯定都是“大雪”那天的雪,且是丰盈的大雪。这其中,是否暗藏着某种微妙呢?
其实,剥离掉知识和其他后天因素,人在本质属性上对自然的感知力是相差无几的,不论你是大名鼎鼎的冰心,还是我那目不识丁的祖母。长年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就更胜一筹了。寒冬将尽时,地面上仍零零星星地遗留着一些残雪,像一帖帖脏兮兮的膏药贴在土地上,赖着不肯走。然而,人们却从草丛里蚯蚓翻出的一坨坨新鲜的泥浆,便知道春天已经从地下潜行而至了,并不需要花朵与草芽来证实——他们有这个把握。在庄稼人眼里,花花朵朵算什么呀,它们顶多像时下那些走场作秀的明星,只为坐实的春天捧捧场而已。
对于自然,豆村人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譬如下霜,在我的家乡就不叫下霜或落霜,而是叫上霜。顾名思义,寒霜是地气化作水汽遇冷而凝成的结晶体。地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想必是带着细弱的微温袅袅升腾的,在它脱离了大地的母体之后,就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改造了——气体死了,而一个新的生命却呈现在世人面前。仅凭这一点,当你再吟诵“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时,或许会洞见白露与寒霜背后潜伏着的天道,深邃、精微与传神,真是妙不可言。
秋末或初冬的清晨,当人们推开门窗,忽见一地素洁、晶莹的寒花,自会不惊不乍地咕哝道:哦,上霜了。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心中早就有谱了。你别以为乡村杂乱无章,人也活得懵懵懂懂、毛毛糙糙,但是他们却深谙自然之道,一阵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朵杏花早开或迟开几天,一只鸟窝垒在高处或地处,他们都能从中窥见奥义。对于霜的认知,我也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一场铺地的严霜君临之前,泥土通常是温润的,天气是晴和的,而空气却十分的干冷。上霜的过程非常微妙,干冷的风像是一根神奇的绣花针或一把刻刀,在潮湿的草叶上,循着叶脉的纹理绣(刻)出一朵朵霜花来。这个过程就好比一根链条,缺了哪一节都不行。这是人工所无能为力的。
下雪也是如此。诗人描摹下雪的情景可以大而化之,譬如“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就这么笼统的不着边际。究竟怎么个“欲”法,并没有明说,也不便明说,只是留下巨大的空白好让我们去想象,去填充。以我的观察与体验,“天欲雪”是有征兆的,就像一个人饥饿了,空瘪的肚肠自会发出咕咕的鸣响。一场大雪即将登场时,寒风瑟瑟,暮云低垂,大地出奇的缄默,天地之间一片黯淡、浑茫,放眼望去,落光叶子的树木挺着腰杆,鸟无踪影,世间的一切都仿佛在静静地等待着某位神灵的君临。
祖母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捂雪”。大凡浩大场景和重要事件,在它们生发之前总不会把底牌一下子亮出来,它们得慢慢地酝酿、集聚、蓄势。比如这大雪的雪,苍天就把它严严实实地捂在怀里,等捂熟了,捂出了大境界,大气魄,便借着呼呼的风势将衣襟猛地一抖,扑簌簌的雪花自茫茫苍穹而降,飘飘洒洒几百上千里,那阵势,不可谓不宏大、壮阔。
此时除了雪,世间的一切都显得渺小了。
我就有这种感觉,置身于纷飞或静谧的茫茫雪原中,仿佛有种无声之声让我不得不安静下来。此时,经过过滤的内心是如此的洁净、丰盈,明澈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与莽莽苍苍的宇宙、起起伏伏的人生这类大问题发生联系,愈发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一场又一场的雪,不违时令地飘落大地,就像一位守信践约的故友,它在该来的时候一定会来。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以上率下,以我的理解,这个“上”,不仅仅指高高在上的权力,而是超越其上的某种不可违逆的轮回之道。天道。其实,它就是一面镜子,既制定法则,也守恒法则,从不像某类人那样,一旦得了势,就可以胡来。
在季节周而复始的轮回中,雪,早春它是檐前滴滴答答的雨水;暮春,它是烟色迷蒙的谷雨;初秋,它是草尖晶莹剔透的白露;深秋,它是叶上的寒露与白霜。一朵来到世间的雪花,循规蹈矩地走着一条上帝设定的路线,它不走偏锋,也不绕道而行,在周而复始的生命轮回中,遵循着自然的律法,它自己也成为别人的律法。
在我的故乡豆村,每年都会降下几场雪,一般以小雪居多。细细碎碎的雪花,像撒荞麦面似的,均匀地随风潜入草丛、林薮、池塘,它们落地的声音,窸窸窣窣的,有点近似于春蚕深夜啃食桑叶发出的沙沙声,优雅动听。因为其小而碎,一般不会在人们的内心引起多大的震动,它落了就落了,化了就化了,就连像我这样关注节气和物候的人,都记不清哪一场小雪落在什么时候。
在二十四节气中,有些时间的节点,给我们的感觉面目比较模糊,譬如雨水、春分、小暑、小满、白露、小寒等,现在的城里人对诸如谷雨、芒种、秋分、寒露等,也是模棱两可,习焉不察,仿佛它们都是与己无干的身外之物,他们似乎只在乎自己的生日,鲜花、蛋糕,酒肉、自拍,呼朋唤友推杯换盏地热闹一番。其实他们忘了,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是自己的生日,也都是自己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天地悠悠,大道轮回,这世间的万类万物,谁又能够逃脱浑然不觉但又如影随形的自然法则呢?
而我的豆村,人们对天道自然是敬畏的,他们不像城里人活在人造的环境中,因而更接地气。送走了一茬庄稼或一位老人,与一场寒霜和一场大雪都息息相关。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节气的轮回之中。我干爹李长青老人,活成了豆村的一棵常青树,他九十多岁还能侍弄庄稼,人们就戏虐地说他是被阎王从花名册上漏掉的人。你猜我干爹怎么说?他说自己不就多见了几场雪嘛,这场不收,下一场说不准就被收走了。他说这话时,还是挺精神的。然而,就在当年冬天的一场大雪降下之后,他老人家说走就走了。他像是从一滴檐前的雨水过度到一朵雪花一样,完成了自己生命的一个轮回。
像我干爹这样的老人,在豆村并不少见。约是七八年前吧,我在寒风刺骨的深冬回到故地,发现几位老人靠着墙根在晒太阳。那冬阳像一盆炭火的余烬,散发着幽微的温度,老人们就借着它取暖,安详地打发余生。当时,我没有看到那些已进入冬天的老人的表情上有任何不安与恐惧,相反,他们却个个都保持着豁达、乐观的情绪,他们谈论死亡就像嗑瓜子一样随意。其中一位年长的扯起话头,他说,于大个子要是能熬过去年的那场大雪,也许还能多活一年。在说者的意识里,去年冬天的那场大雪,就是横亘在于大个子命途上的一道大坎。另一位老人则反唇相讥:就算他熬过了去年那场大雪,还有下一场雪呢。这话一经说出,在座的老人都沉默不语了。是的,他们现在正处在“下一场”大雪来临之际。自然界的一场大雪,诗人会说“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而当“下一场”大雪真的降临大地,这些在冬阳下谈笑的老人,又会有谁像竹子一样被折断呢?
似乎只有天知道了。
不过,我在次年大雪之后再次回到豆村时,发现去年晒太阳的老人中,又被雪走了两个。
而今,一路穿越过无数次霜降、小雪、大雪的我,已经越来越接近冬天了。有时我会想,属于自己生命里那最后的一场大雪,也许还在某处酝酿着,它肯定会在该出现的时间出现。它是我的终结,也是我的开始。
人能够在一朵雪花上轮回,想想,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物候记
说不清从何时起,我对物候的变化产生兴趣,初秋一枚辞枝的黄叶,燕子去后留在老屋桁木上的空巢,抑或残雪消融从泥土下拱出的一只惊魂未定的甲壳虫。总之,物候最初给我的感觉是神秘的,它远远超出我的认知和想象力。
小时候养过一种麻色羽毛的鸟,这种鸟习惯把巢筑在阳坡的浅草地上,至于它们什么时候产卵、孵化幼鸟,则是一笔糊涂账,后来还是白茅提醒了我。初夏时节,地里的麦子抹上一层嫩黄,白茅抽出如雪的花穗,小雏雀即将出巢了——物候就这么灵验,屡试不爽。再后来,我对物候的观察范围逐渐扩大,惊蛰蚯蚓翻浆,春分冬麦起势,寒露野蜂绕檐,在节律的轮回中,捕捉大自然的蛛丝马迹。自从操瓢文学,我便将自己对物候的观察所得写进作品,于是有了《乡村的风》、《节气》、《在一朵雪花上轮回》、《在一滴露珠里行吟》、《请不要打扰夜晚》等,物候与文学攀上了亲戚。
早年戎马倥偬,脱下军装后又多次转徙,人生的轨迹飘忽不定,使我的物候观察时断时续。记得在苏鲁接壤地带当兵时,我连续多年在沭河边的一个固定位置,观察“初霜”与“解冻”,八十年初代在淮水之滨记录芦芽何时破土、飞白,小蝌蚪需要多少天才能变成青蛙。可惜那些珍贵的观察日记都散佚了。但是,只要生活稍稍安定下来,我又从头再来——积习难改啊!
十四年前移居江南小城池州,住在牧童遥指的杏花村,我开始观察杏花。烟雨江南地,杏花要比我的老家皖东早开一周左右,早不了多少,也晚不了多少。让我费思的是,一株位于杏花大道老石油站门前的杏树,论树龄、土壤和附近的环境,与周围其他杏树并无差异,但它的花期要比其他同类提前两到三天,暖春也好,倒春寒也罢,年年如此。有一年的二月底,突然窜来一场风雪,我估摸那株早杏的花期可能要推迟了,谁知它竟像掐着时间赴约的情人。我翻翻往年的观察日记,只差几个时辰。一株杏树放在宏大、深邃而阴晴冷暖无法把握的时空中,居然能把自己的花期控制的如此精准,的确让我敬佩。然而,就像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那株年年抢着开花的杏树,果实却小如泥丸,成熟期也晚了许多。有了那株早杏作参照物,每至杏花季,外地朋友预约来江南看杏花,我会准确地报出具体日期。
一个人,并非出于职业需要,把观察物候这件无关生活轻重的事,断断续续延续了几十年,连我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也许起初只是出于好奇,继而引发兴趣,而兴趣这东西最靠不住,犹如烟花易冷,你得不断地给它输入能量,渐渐形成积习。积习似一件用皮肤做的衣服,不是想脱就脱的了。
家搬到市郊后,给我观察物候带来了许多便利。此时的我虽然老了,好在心无挂碍,有了更充裕的时间跟大自然相处与交流。
新居悬在七楼,轩敞的西窗正对着平天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凭窗看湖。此时的平天湖很安静,我也安静。安静人看安静湖,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相看两不厌,唯有平天湖,是有那么一种欲说已忘言的味道。
连续几年的观察,我对平天湖的性格、脾气已了然于心,有个什么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比如,不用听气象预报,只需瞄一眼湖水颜色的深浅,水边芦苇摇摆的姿态,就知道当天刮的是什么风,几级。开始只是猜测,并将猜测的结果与官方权威发布的数据相对照,不到一年工夫,两者的数值几近吻合。大地上的一切事物,看似不可捉摸,变幻无穷,其实都是有征兆、规律可循的。比如风的量级,你可以通过对一株特定芦苇的长期观察,从它摆动频率、幅度的大小,感知风力。当然也会偶尔看走眼,那多半是光照和雾岚从中作祟。
现时,我的观察物已从杏树转移至他物身上。在湖的东岸,闲置着许多从农民手里流转过来而未开发的土地,给外来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提供了可乘之机。三年前,它们还只是零星地点缀在本土草木中间,东一株,西一簇,彼此孤立无援,然而不出两年便一统江山,以压倒性优势奠定了物种的霸主地位。这种夷物,繁殖力和适应性特强,毁土占地,凡是成片生长的地方,土壤的营养被其榨取殆尽,本土植物压根儿就不是其对手。有关部门虽调集力量斩除过,但因对此物的物性不是很了解,总是不能斩草除根。我根据自己的观察,记录下一枝黄花生长史,建议在它们开花后七日左右刈割,一来所有该开的花都开了,目标暴露无遗;二来趁其籽实尚未成熟,斫之断子绝孙。今年霜降前后,一场围剿一枝黄花的行动在关键节点上展开,一时间横尸遍地。
物候在大雁身上的表现尤为突出,而平天湖又是南迁候雁的驿站,自然也是我观察的重点。翻开观察手记,候雁的行踪一目了然:
2017年10月11日19时,晴。初雁至。目测约七八只。
2018年10月10日20时,小雨。闻雁声,未睹其物。
2019年10月15日21时,月色皎洁。雁始至。其阵横空,众,不可细数。
2020年10月9日18时,阴,欲雨。雁自东北来,其声嘹唳,绕湖数匝,去。
今秋大雁来的早于往年。10月3日晚上我在湖边散步,清风拂面,秋意正浓,第一梯队雁群便早早抵达平天湖,连续几个黄昏与夜晚,雁鸣声不绝于耳。这一次,它们留了下来,白天飞往西南的升金湖和长江的落雁洲,傍晚再回到平天湖。这种现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雁恒自东北来,常往西南去,很少有返程的,除非个别体力不支或受伤的孤雁。相较于前几年,辛丑年的雁群明显少了许多,过程由此前的一个多月缩短为一周。我好生纳闷,难道大雁改变了南迁路线?
到了11月初,一股超强寒流席卷西北和东北大地,降下近百年同期罕见的大雪,远隔数千里的江南一夜进入寒冬。就在我将雁事淡忘之际,11月2日黄昏时分,数支超大雁群背负着青霜,凌空排挞而来。想必是追星赶月太急,体力透支过多,它们一见了空旷的平天湖,把与生具有的警惕丢之脑后,欢叫着俯冲而下,像游子一头扑进母亲温暖的怀抱。在我写这篇文字时,时令已进入小雪,然而北方的雁群还在一拨一拨地往这边赶,嘎嘎的叫声响彻整个夜晚。夜半醒来,借着寒星的微光,湖面上起起落落的雁群身影依稀可见。
处在雁道上的平天湖是仁慈的,它默默的迎来送往,直到最后一支雁群离它而去。
物候里面藏天道。在大自然的一个又一个轮回中,感知每一种生命的花开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