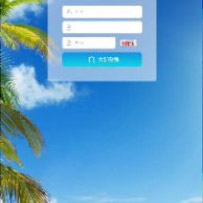离开故乡已经一月有余了。故乡的人与事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几乎每晚都在梦中度过,那些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场面,时时出现。梦醒之后,一种莫名的惆怅袭击我的心扉。
异乡的秋天总使人感到透心的凉。小区那些花草树木总感觉阴阳怪气的,有的齐头并进,有的蜷缩着身躯,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甚至乱了季节似的挤眉弄眼的邀功请赏。这里的树木没有故乡那些杂乱无章的树木那种昂扬奋发、随心所欲的恣肆。
行人行色匆匆,擦肩而过,面无笑色,有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即使在逼仄的电梯相遇,要么仰视天花板,要么低头拨弄手机。每个人好像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很莫名其妙,为什么我对城市产生如此抵触情绪呢?会不会与20年前陪父亲到城里看病的一次经历有关呢?
那年父亲病得很厉害,无情的病痛整日整夜折磨着他,家门口的医生无计可施,我最后下定了决心,“卖粮食吧!”先救父亲要紧,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把仓里的粮食卖了,忐忐忑忑乘着车带父亲到城里看病。刚下车走了一段路,我和父亲同时看到前面一个小伙子一沓现金掉在地上。我和父亲都很诧异,但我立刻提醒自己:天上不会掉馅饼,恐有诈。我赶紧捏捏父亲的手,示意他别捡。一向胆小谨慎的父亲一下子有些紧张。我通过拉着父亲的手的温度,能感知父亲心里是多么的恐惧!一会我们到医院候诊室,刚才那个掉钱的小伙子也来了,他身穿西服,白衬衫,坐在长椅上。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可能父亲也认出来了,父亲惊慌失措的样子更害怕了。几十年过去了,那次上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因为是第一次到大城市看病,没有看病的经验,清早母亲给我们每人做了一碗面条吃,看病的时候,好不容易排上队,不知道看内科要空腹,我们只得留宿一晚等明天再看。记得我和父亲住在医院附近一个很实惠的宾馆,一晚每人10元钱,还负责供应开水。我和父亲都睡不着,父亲不知是受到了惊吓还是舍不得钱。他翻来覆去,终于开口了:“毛伢(我的乳名),那个药钱能退掉吗?”其实那一粒药只是检查前的辅助作用的药。也就是做一个全身的CT检查费要一千多元,父亲以为是那一粒药需要那么多钱。在那八、九十年代,一千多元对一个农家来说也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安慰父亲:“别担心钱,我们兄弟几个有办法,你睡觉好了,只要你没事,我们就开心。”但是,那次到大城市,最终也没有救下我父亲的命。这将是我永远的痛!
站在故乡之外的高楼向远处眺望,望不到故乡的影子。每天必做的功课,打开手机遥控,在小小的摄像头里搜索故乡那小小的一片天地。那棵高大的香樟树还是屹立在院子里西边,像撑起的一把大伞,树影婆娑。深秋季节里的枇杷树,不紧不慢,酝酿着绿意,因为它要在寒冬塑造一树洁白的精灵。枣树、桃树、梨树,还有石榴、柿子,它们已经告别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一步步向繁花似锦的春天迈去。鸡呢、狗呢、猫呢,它们也纷纷争抢镜头,两只小鸡居然大打出手,一只飞奔冲向另一只看起来有些瘦弱的小黄鸡,但它万万没想到的是,小黄鸡居然展开翅膀,伸着脖颈摆出一副一决雌雄的架势,这招果然灵验,那只气势汹汹的芦花鸡连忙止住脚步,悻悻地离开了。小黑狗正在竖起耳朵,东张西望,因为这是平时我回家的时间,也是它跑来用头蹭我的裤脚的时候。三只小黄猫大概是习惯了寂寞,蜷缩着身子互相搂抱在一起睡在门前的笤帚上,安然入睡……
晚上,站在窗前,抬头凝望,一轮圆月匆匆地在云层里穿梭。一阵寒意无端地袭来,秋意正浓,思绪亦浓,乘着秋风,思绪飞向遥远的故乡。这个时候,故乡田野里那收割完的庄稼只剩下一排排谷桩了吧?捡螃蟹的时候也该到了,夜晚,拿着手电筒,在河滩上,油菜地里,稻田里……那横行霸道的小家伙送来了美味佳肴。清晨,身穿皮裤的老人左手拎着网兜右手握着木把铁锹,一天的酒钱就藏在装虾的网兜里,笑意荡漾在额头上的皱纹里。
最难忘,小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天麻麻亮就被母亲唤醒,捡稻穗是这个季节农村娃必做的功课。田野里,寒霜覆盖在碧绿的紫云英上,露水还没有被太阳收走,一群小毛孩便散落在田间地头,那一株金黄的稻穗躺在铺满紫云英的田里,那便是孩子们的惊喜。手背冻得通红,鼻涕挂在嘴唇上,实在有些碍事就用袖口揩一下,白色的鼻涕沾满衣袖,跟地上的白霜一样。我们兄弟几个齐上阵,每人夹了一小捆捡拾的稻穗,满载而归。母亲早已准备了一筲箕红薯留给我们充饥……想想那甜丝丝的红薯味,至今仍然回味无穷啊!那时的生活虽然很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回味起来却是满满的幸福。
很长时间没有闻到家屋背后那热闹的鸟鸣声了。麻雀叽叽喳喳的叫个不休,似乎旁若无人。鹁鸪很斯文地告诉同伴,“咕咕”地声音不竖起耳朵会被八哥的吵架声淹没了。修养性很差的八哥一大早就闹腾不止,晨光都被抖落一地。偶尔也能听到喜鹊的声音,“喳喳”两声,给黎明增添了许多喜气。小时候常听母亲所言:“喜鹊叫喳喳,好事到我家。”成年之后才明白,母亲无时无刻不对家庭充满了美好的期盼。
来到城里之后,那些一度有些厌烦的鸟声便渐渐远去。充满耳鼓的全是隆隆的机器声,整日整夜,无休无止,挖掘机,推土机,张牙舞爪,竭尽所能,恨不得把整个地球都翻个底朝天。它们就像一只只饿狼一样,杂草,树木,连同小区居民种的绿色蔬菜,哪怕嘴里夹杂着石子,全都吞进肚里。
自然赶走了弱小无助的小鸟。一日到小区楼顶去晾晒衣服,突然发现两只灰雀站在高墙沿上,好像没有往日的欢声笑语似的,当我们目光相遇时,它似曾相识一般,彼此产生邂逅的惊喜。下楼后,依然惦记了很久很久……
昨天在一方小小的水塘旁与一对喜鹊相逢。一只立在水塘旁边,一只站在电线杆上,他们可能是一对恩爱夫妻,水塘边的那只“叽叽喳喳”呼唤几声,意思是“快来看呀,这儿有谁啊!”站在电线杆上的那只也“叽叽喳喳”道“是真的吗?我来啦!”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在这铜墙铁壁的都市,寻得一方水塘那是何等的不易啊!
大概是它们太惊喜了吧。“喳喳,喳喳……”一唱一和,叫得更欢,那声音真好听,或许从小受母亲的熏陶,对喜鹊情有独钟,一身乌黑发亮的羽毛连同翅膀,仿佛披着一袭黑长裙,搭配一件贴身的白衬衫,黑白分明,别致精巧。见到它,我仿佛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它也朝我“喳喳”的打个招呼,此时我觉得它们就是故乡的那对喜鹊。它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俨然没有一丝都市里的俗气,它不顾迢迢万里的征程,风尘仆仆,寻到这里来,不就是为了追寻自己的信念吗?
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什么都得学,饮食起居,烧火做饭,洗衣浆衫,就像是脱胎换骨一样。正所谓“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万事都得去想啊。走进厨房,回忆和想象并用,记得小时候母亲在田地里干活,叫我在家做饭,手把手地教,从淘米到做饭,从炒菜到焐茶,样样都得学。土灶柴锅,那滚滚柴烟布满整个厨房,连栖息在厨房里的蜘蛛、蟑螂、蚊蝇,甚至躲在地灰里的“灰鳖”也纷纷外逃。尤其是阴雨天,柴烟不出屋,简直把人熏得眼泪哗哗直流。母亲说,饭在锅里,如何判断饭已经烧好了呢?就看锅盖上方的烟汽,烟汽逐渐向中间聚拢就说明饭烧好了,也可以用鼻子闻一闻,闻到了饭香就立即停止给灶膛添柴,说明饭已做好。尽管谈不上美味佳肴,全家人总有一口现成的饭吃。那个不温不饱年代的人们能都填饱肚子已经是最大的奢侈。最难的是“焐茶”,灰褐色瓦壶添满水,挑一汤匙茶末,用“柪子”的一个齿拗住茶壶的手把,把它塞进灶膛用柴火的余温把茶焐热。那时的人们,胃是铁做的,不管瓦壶里的茶开与否,“咕咚咕咚……”喝进肚里,照样开工干活,即使来不及到灶膛里去摸水壶,拿起葫芦瓢在水缸里舀起一瓢水,一饮而尽,既解渴又方便。
隔壁是李大妈家的厨房。土砖瓦屋,相邻的墙壁凿一个大窟窿,可以容纳一只猫穿梭来往,平时谁家缺一升米,少一勺油或盐什么的,隔洞喊一声,既可解燃眉之急,又传递邻里乡亲的友善。后来也成了我与长辈之间搭起的桥梁。每当我在厨房烟熏火燎的时候,大妈不时在洞口喊一声:“毛伢(我的乳名),菜放盐了吗?饭烧开了吗?饭烧好后别忘焐茶哟!”我在这边的洞口立即应一声:“知道了。”
早年,老屋没有了,大妈也已去世了,只留下不尽的思念……
如今,漂泊在外,他乡容纳不下我的灵魂。望着窗外黎明时的月亮,它高高地悬挂在西边的天空。现在一丝云彩都没有,连风都静止了。月亮孤零零地定格在寒冷的楼顶。小区终于可以安睡了,连路灯的光也隐隐地退去,把所有的世界让给了月光,柔和的月光铺满了楼顶,又穿过树的缝隙,落在枯草上,漏在地上……
乡愁却彻夜难眠!久违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