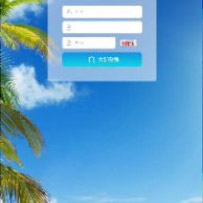一天傍晚,与妻步行回家,半路上妻想起落了东西在孩子姥爷家,要我在桥上等她,她自回去取。
我依言在桥上等,傍晚的微风沿着河道贯穿我的身体,我眺望夕阳,晚霞印在河水的柔波里,微微荡漾,闪耀着红艳艳的波光,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般绚丽的景致我竟已许久未见,那么熟悉,却又如此陌生,可我知道,它一直就在我的身边,而我总是熟视无睹,许久是多久,竟无从记起,不由得心生愧意。
从小到大,每天也不知要从这桥上过几次,也从来无暇细数,总是匆匆而过,很少能停下脚步,仔细地打量一眼这座风雨相随了几十年的,故乡的桥。
县城始建于明万历三年,因城内有钵盂山,登临可望江流之胜,顾名思义,取名曰望江。河道原为长江故道,将县城分为南北,桥是这座江南小城的标志性建筑,桥建成后,就被取名新桥,而这条原先无名的河,就顺理成章的叫做新桥河。
新桥不新,因为它至少已与我年龄相仿,至于是何年所建,我已懒于考证,自我出生之前,它就已经坐落在这条河上,桥不能语,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言行之中,“去桥那边,”“在桥上等我,”“家在桥南面,过桥就不远了”…
桥是砖混结构,宽约十四五米,长约七八十米,水泥栏杆扶手,凭栏而眺,河道弯弯,波光粼粼。桥下三个砖石垒砌的桥墩,是儿时我们这些顽劣孩童嬉戏弄潮的跳台,每当夏至,河水丰沛,下午放学过后,沿河两岸的住户,小到六七岁的孩子,大到五六十岁的老人,只要会水的,都会钻到河里游上一会,一则消暑,二则洗浴,三则健身,那时的河水很清,清得让人想做河里的一条鱼。
泳者之中那些水性好的,都会以桥为目标,大家都从下水的位置往桥的方向游,先至者爬上桥墩,双手抱膝坐在桥墩上,扬着脸接受我们这些落后分子的膜拜,等到我们即将爬上桥墩,他们又一个猛子扎进河里,等到三四十秒之后,在几十米外的水面外冒出头来,回头给我们一个揶揄的笑,振臂划水而去。
站在桥上,我能看到河道左边的一个小河湾里,父母亲住的房子的顶,桥的右边拐下去,再走两百多米,就是岳父母的家;工作单位在桥的北面,家在桥的南面,进入新世纪之后,桥身得以加宽巩固修缮。
以桥为标,北面有始建于宋代的文庙,庙入口处有石桥,名曰状元桥;钵盂山边有创建于元代,距今已六百余年的青林古刹,有牌坊楼,有雷阳书院,书院里曾有凤凰墩和魁星阁,桥南面一公里,原有座奎文塔,建于道光年间,塔身六角五层,青砖砌成,当地人都叫宝塔。这些古建筑或毁于战火、动乱和水患,几经沧桑、几度兴废,在近年在几级政府的努力下有些得以重建或修葺,如今都列入了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的或成为搜索引擎里的一个名词,亦或成为当地老人们茶余饭后口中念兹在兹的往昔岁月了。
桥下游一公里处,还有一座小桥,比新桥窄短了许多,名气却大了许多倍,此桥名曰“卧冰桥,”是为了纪念中华传统经典文化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故事,孝为百善之先,感天动地,教化后世,是中华美德,何其有幸,中华二十四孝有三孝都发生于此,故此望江这块美丽的土地也被称之为“三孝故里”或者“三孝之乡。”
过桥往南六七公里,就到了江边,那里有座码头,叫华阳码头,因为是停靠大客轮的,所以也叫大轮码头,这个码头,曾经是长江汉口港以下,最小的一座客运码头,作为对外的窗口,这座码头是那些时代多少望江人走向外面的世界,实现梦想的起点,直到二零零五年,长江客运航线全线停航,这座码头的功能作用被日新月异的公路及铁路交通网所替代,特别是飞架于临近长江之上,那些让天堑变通途的江桥,到了二零一六年,一座名叫望东长江大桥直跨县境,望江人民有了自己的长江大桥。
桥,似一粒粒的纽扣,将错落交织在山川泽国里的公路铁路串联起来,也将故乡与人联接起来,它们和故乡的风雨一起,偶而浮现于每个人的梦中,不管他们身在何处,都会勾起他们内心底的乡愁绪绪,挥之不去,每个人与故乡之间,只有一座桥的距离。